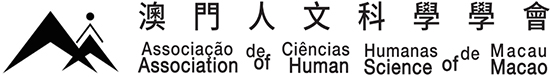三 政 治 篇
1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學而》
【譯文】孔子說:“治理具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對政務要恭敬慎重對待,辦事要講信用,節約費用,愛護民人,使用百姓要有一定的時間。”
2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為政》
【譯文】孔子說:“用道德來治理國政,便會像北極星一樣,在其位置上,別的星辰都環繞著它。”
3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為政》
【譯文】孔子說:“用政令來引導他們,用刑罰來規戒他們,民人只是暫時地免於犯罪,卻沒有廉恥之心。如果用道德來引導他們,用禮教來規戒他們,民人不但有廉恥之心,而且能自我改過。”
4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為政》
【譯文】魯哀公問道:“怎樣做百姓才會服從?” 孔子答道:“選用正直的人,放在惡人之上,百姓就服從;若是選拔惡人,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會不服從。”
5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為政》
【譯文】季康子問道:“要使民人恭敬、忠心並互相勉勵,應該怎麼辦呢?” 孔子說:“你對待他們態度莊重,他們就會恭敬;你孝順父母,慈愛幼小,他們就會對你盡忠竭力;你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他們就會互相勸勉了。”
6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為政》
【譯文】有人對孔子說:“你為甚麼不參與政治?” 孔子說:“《尚書》上說,‘具有孝的品德,就是要孝順父母,友愛兄弟,並把這種風氣影響到政治上去。’這也就是參與政治啦,為甚麼一定要做官才算參與政治呢?”
7 定公問 :“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八佾》
【譯文】魯定公問:“君王使用臣子,臣子服事君王,各應該怎樣做?” 孔子答道:“君王應該依禮節來使用臣子,臣子應該盡忠心來服事君王。”
8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八佾》
【譯文】孔子說:“居於統治地位的人不寬宏大量,行禮之時不恭敬認真,參加喪禮不悲哀,這種樣子我怎能看得下去呢?”
9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里仁》
【譯文】孔子說:“能夠用禮讓來治理國家嗎?這有甚麼困難?如果不能用禮讓來治理國家,又怎樣來對待禮儀?”
10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公冶長》
【譯文】孔子評論子產,說:“他有四種行為合於君子之道:他的行為莊重,他服事君王恭敬,他管治民人有恩惠,他使用民人合於道義。”
11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
【譯文】孔子說:“泰伯,那可以說品德為最高了。屢次把天下讓給弟弟,百姓簡直找不出恰當的詞語來稱贊他。”
12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泰伯》
【譯文】孔子說:“只知恭敬卻不知禮儀就會疲倦,只知謹慎卻不知禮儀就流於懦弱,只知勇敢卻不知禮儀就會闖禍,只知心直卻不知禮儀就會傷人。君子用深厚感情對待親族,百姓就會追求仁德;不遺棄其老朋友,百姓就不會冷淡無情。”
13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泰伯》
【譯文】孔子說:“舜和禹真是崇高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卻 一點也不為自己。”
14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泰伯》
【譯文】孔子說:“堯作為天下的君主真是偉大!真是崇高啊!只有天最高最大,只有堯能夠效法天。他的恩德廣大,百姓簡直不知道怎樣贊美他。他的功績真是太崇高了,他的禮儀制度真是光輝燦爛啊!”
15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泰伯》
【譯文】舜有五位賢臣,天下太平得治。武王也說過:“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 孔子因此說道:“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唐堯、虞舜以及周武王之時,人才最興盛。然而武王十位人才之中還有一位婦女,實際上只是九位罷了。周文王得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向商紂稱臣,周朝的道德,可以說是最高的了。”
16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泰伯》
【譯文】孔子說:“禹,我對他沒有任何批評。他自己吃得很差,卻盡力孝敬鬼神;穿得很差,卻把祭服做得極華美;住得很差,卻盡力於溝渠水利。禹,我對他沒有任何批評啊。”
17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先進》
【譯文】孔子說:“我們所說的大臣,是用道理來服事君王,如果行不通,寧肯不做。”
18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顏淵》
【譯文】子貢問怎樣去治理政事。孔子說:“糧食充足,軍備充足,政府取信於民。”子貢說:“如果迫不得已,在上述三者之中可以先去掉哪一項?” 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說:“如果迫不得已,在餘下兩者之中可以再去掉哪一項?” 孔子說:“去掉糧食。因為自古以來誰都免不了一死,但如果民人對政府失去信心,政府就站不住腳了。”
19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顏淵》
【譯文】齊景公向孔子問政事。孔子答道:“君王要像個君王,臣子要像個臣子,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景公說:“對呀!若是君 王不像 君王,臣子不像臣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即使有糧食,我能吃得著嗎?”
20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顏淵》
【譯文】子張問政事。孔子說:“身居官位不倦怠,執行政令要忠實。”
21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顏淵》
【譯文】季康子向孔子問政事。孔子答道:“政的意思就是正直。您自己帶頭正直,誰敢不正直呢?”
22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顏淵》
【譯文】季康子苦於盜賊太多,向孔子求教。孔子答道:“假若您不貪求太多的話,就算獎勵偷竊,他們也不會幹。”
23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顏淵》
【譯文】季康子向孔子請教政事說:“假若殺掉壞人來親近好人,怎麼樣?” 孔子答道:“您治理政事,為甚麼要殺人?您如果要行善,百姓就會善良起來。君子的作風好比風,百姓的作風好比草。風吹到草上,草就會傾倒。”
24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 【譯文】子路問政事。孔子說:“自己首先帶頭,工作且要勤勞。”子路請多講一點,孔子又說:“不要懈怠。”
25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路》
【譯文】仲弓做了季氏的總管,向孔子問政事。孔子說:“給執事人員帶頭,不計較人家的小錯誤,提拔優秀人才。”仲弓問:“怎樣去識別優秀人才把他們提拔出來呢?” 孔子說:“提拔你所知道的;那些你不知道的,別人難道會捨棄他們嗎?”
26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路》
【譯文】子路對孔子說:“ 衛 君等著您去治理國政,您準備首先做甚麼?”孔子說:“那一定是糾正名分的不當使用罷!”子路說:“您怎麼迂腐到如此地步哇!那有甚麼可糾正的?”孔子說:“真粗野啊,仲由!君子對於他所不懂的,大概要持保留態度。名分使用不當,言論就不合道理;言論不合道理,事情就不能辦好;事情辦不好,國家的禮樂制度也就推廣不起來;禮樂制度推廣不起來,刑罰也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百姓就會惶惶不安,連手腳放在哪兒都不知道。所以君子使用一個名分,一定要有一定的道理,有道理才一定行得通。因此,君子說話論理時一點馬虎都不行。”
27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子路》
【譯文】孔子道:“統治者講究禮節,百姓就沒有人敢不尊敬;統治者符合道義,百姓就沒有人敢不服從;統治者誠懇信實,百姓就沒有人敢不說真話。”
28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路》
【譯文】孔子說:“〔統治者〕本身行為正直,不用發命令,事情也行得通;〔統治者〕本身行為不正直,雖然發出命令,百姓也不會服從。”
29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路》
【譯文】孔子到衛國,冉有駕車。孔子說:“人口真稠密啊!”冉有問:“人口多了,又該怎麼辦呢?” 孔子說:“使他們富裕起來。” 冉有又問:“已經富裕了,還要怎麼辦?。” 孔子說:“教育他們。”
30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路》
【譯文】孔子說:“‘善良人治理國政連續一百年,就可以克服殘暴免除殺戮了。’這句話真說得對呀!”
31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路》
【譯文】孔子說:“如果自身得以正直,治理國政還有甚麼困難呢?如果連本身都不正直,怎麼去糾正別人呢?”
32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子路》
【譯文】魯定公問:“一句話可以使興盛國家,有這事麼?”孔子答道:“說話不可以這樣地肯定。不過,常言道:‘做 國 君很難,做臣子也不易。’假如知道做 國 君的艱難,自然會謹慎認真工作,不就是一句話便興盛國家麼?”定公又問:“一句話可以喪失國家,有這事麼?”孔子答道:“說話不可以像這樣地肯定。不過,常言道:‘我做 國 君沒有別的樂趣,只是我說的話沒有人敢違抗我。’假如你說得對而又沒有人違抗,不也好麼?如果你說的話不對也沒人敢違抗,不就是一句話便喪失國家麼?”
33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子路》
【譯文】葉公問怎樣治理政事。孔子答道:“讓周圍的人高興,讓遠方的人投奔。”
34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路》
【譯文】子夏做了莒父的縣長,問怎樣治理政事。孔子答道:“不要急於求成,不要貪圖小利。急於求成,反而達不到目的;貪圖小利,就辦不成大事。”
35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路》
【譯文】樊遲問仁德。孔子答道:“平日容貌態度端正莊嚴,工作認真敬業,為人忠心誠意。即使到未開化地區,這幾種品德也不能丟掉啊。”
36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子路》
【譯文】孔子道:“用未經教導和訓練的民人去打仗,是拋棄他們。”
37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憲問》
【譯文】孔子說:“國家政治清明,說話正直,行為正直;國家政治黑暗,行為正直,言語謙避。”
38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憲問》
【譯文】子路問怎樣服事君王。孔子道:“不可以欺騙他,但可以冒犯他。”
39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憲問》
【譯文】孔子說:“統治者如果事事依禮而行,百姓就容易聽從使喚。”
40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憲問》
【譯文】子路問怎樣才能做一個君子。孔子答道:“修身克己,認真做事。”子路問:“這樣就夠了嗎?” 孔子說:“修身克己,與人安睦。”子路又問:“這樣就夠了嗎?” 孔子說:“修身克己,使百姓安居。修身克己,使百姓安居,堯舜大概還沒做到哩!”
41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衛靈公》
【譯文】孔子說:“無所做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甚麼呢?莊嚴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罷了。”
42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衛靈公》
【譯文】子張問如何才能使自己的主張行得通。孔子答道:“言語忠誠信實,行為恭敬認真,即使到了荒蠻地區,也行得通。說話不忠誠信實,行為不恭敬認真,就是在本鄉本土,能行得通嗎?站立的時候,就看見“忠誠信實恭敬認真”幾個字在我們面前;在車上,也看見它刻在前面的橫木上,這才能使自己到處行得通。”子張把這些話寫在衣帶上。
43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衛靈公》
【譯文】顏淵問怎樣去治理國家。孔子答道:“用夏朝的曆法,坐殷朝的車子,戴周朝的禮帽,音樂就用韶和武。捨棄鄭國的樂曲,遠離小人。鄭國的樂曲淫靡,小人危險。”
44 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季氏》
【譯文】孔子說:“我聽說過:無論是諸候或者大夫,不必擔心財富不多,只須擔心財富不均;不必擔心人民太少,只須擔心境內不安。若是財富平均,便無所謂貧窮;境內和平團結,便不會覺得人少;境內平安,國家便不會傾危。做到這樣,遠方的人還不歸服,便再修仁義禮樂來召喚他們。”
45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堯曰》
【譯文】子張向孔子問道:“怎樣就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答道:“尊重五種美德,排除四種惡政,這就可以治理政事了。”子張問:“五種美德是甚麼?”
孔子說:“君子給民人以實惠,而自己卻不浪費;勞動百姓,卻不招致怨恨;有正當欲求但不貪心;從容矜持卻不驕傲;儀態威嚴而不兇猛。”子張說:“給民人以實惠,而自己卻不浪費,是甚麼意思呢?”孔子答道:“就民人能夠得利之處而使他們得利,這不就是給民人以實惠,而自己不浪費嗎?選擇適合工作的時間和環境去使用百姓,又有誰會怨恨呢?自己需要仁德便可得到仁德,又貪求甚麼呢?無論人多人少,無論勢力大小,君子都不敢怠慢他們,這不就是從容矜持而不驕傲嗎?君子衣冠整齊,目不邪視,莊嚴使人望而敬畏,這也不是儀態威嚴而不兇猛嗎?”子張問:“四種惡政又是些什麼呢?”孔子答道:“不加教育便加殺戮叫做虐待;不加申誡便要成績叫做暴戾;起先懈怠,突然限期完成叫做陷害;好像給人財物,出手慳吝,就叫做像執事的帳 房 先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