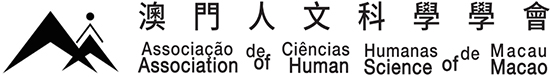中國大陸學者論文
倫理學從傳統到現代形態的範式轉換
趙敦華
一、傳統倫理學的範式批判
傳統倫理學有三種類型:目的論、義務論、功利論。這三種類型有以下兩個共同特點。
第一,它們都是規範倫理學。傳統倫理學認爲,規範來自於價值,而不是來自於事實;價值與事實是二分的,價值是應然,事實是實然,這是傳統倫理學的基本設定。但是傳統倫理學的許多規範恰恰是從人的存在的事實中推導出來的,這就和傳統倫理學的基本設定是有矛盾的。不過,傳統倫理學認爲他們對人的存在事實的各種判斷都是天經地義、勿庸置疑的自明真理,而不是有待考察的事實。這樣就掩蓋了矛盾。比如,目的論對人性事實的判斷是:人都是追求幸福的,幸福是所有追求的終極目的,但是,幸福爲什麽會成爲人生的最高目的?人一定會追求“至善”嗎?目的論認爲這些問題是不須討論的。又比如,義務論認爲人的義務是從道德律來的,而道德律反映在每個人的良心之內,這也是自明的道理。但是,人是不是都有良心?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良心?這些問題義務論是疏於繼續考察的。同樣,功利論假定的人性基本事實是:人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功利就成爲善良價值的來源,但是,人爲什麽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爲什麽不能毀滅自己的利益?功利論認爲相反的假定是匪夷所思的。
第二、它們都有心理主義的傾向。所謂心理主義傾向,就是用人的心理狀態來解釋和描述道德規範。心理狀態一般被分成三種:知、情、意。從“知”的角度研究倫理學即理智主義,強調認知功能在道德行爲中的作用,理智主義與目的論有密切關係;從“意”的角度研究倫理學即意志主義,強調意志在道德行爲中的作用,意志主義與義務論有聯繫;從“情”的角度研究倫理學即情感主義,它與功利論有很大關係。心理主義的問題在於:它往往會忽略倫理行爲常常是人們的一種習慣的産物,並不總是伴隨著意識活動,有時甚至是無意識、下意識的,並不是作任何一件道德行爲都有明確自覺的理智、情感、意志的參與,如果真的要是經過一番“知、情、意”的算計和選擇,就往往不“行”了。“倫理”這個詞就是最初從希臘文中的“習慣”(ethos)而來的,從詞源上來講是這樣;從中國歷史上看,孟子首先講“五倫”,人倫也是一種習慣性的人際關係。人和人交往中的習慣並不總伴隨著意識,這並不是說他沒有這樣的意識,而是說他在行爲時並不需要這樣的考慮。如一個英雄做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事,事後記者採訪他時會問:“你當時是怎麽想的?”英雄往往都是這樣說的:“我什麽也沒想,當時就想救人要緊”。這就是道德行爲的真實狀識,因爲他已經養成了這個習慣,他並不需要意識始終支配自己,而“知情意”就是要求意識狀態,而且是個人意識狀態,如此描述道德行爲,是不符合實際狀況的。
總之,通俗一點說,傳統倫理中的規範倫理學把人想得太好了,倫理學的心理主義又要人想得太多了;而這都是和道德實踐的真實狀況有出入的。這就是傳統倫理學存在的根本問題。傳統倫理學家們也覺察到了傳統倫理學理論和實際生活有格格不入之處,爲了打破這些隔膜,他們又加了很多補充性說明,比如中國有對“知行關係”的探討,對“經權”問題的探討。在西方,比較著名的有“蘇格拉底悖論”,即“德性就是知識,無人有意作惡”。蘇格拉底爲了解釋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惡,只好加了“作惡是因爲無知”的補充說明,可是生活中有多少錯誤是明知故犯的啊!經權關係在西方思想史上稱爲“決疑法”(casuistry),即在實踐中出現與原則相悖的情況時,加進來一些補充性原則,使實踐與原則恢復一致,使實踐在道理上講得通。倫理學本身是實踐的學問,在一個徹上徹下的倫理學理論中,知和行、經和權的關係本來不應該有問題的,至少不應該是基本問題,嚴重的問題。如果出現了這種性質的問題,那就說明倫理學理論本身有問題。
二、現代倫理學的範式轉換
西方倫理學界也意識到了這種理論困境,出現了一些新的道德哲學學說,比如正義論、德性論、商談倫理學等等,它們意在彌補傳統倫理學的缺陷,但它們還是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傳統倫理學的困難。正義倫與商談倫理學從根本上講,還是屬於規範倫理學的範圍,要建立一些新的原則和規範來指導道德實踐。德性論因此反對正義論和商談倫理學的規範倫理;德性論採取歷史的敍事法,麥金泰爾的《德性之後》和《誰之正義?何種理性?》實際上是用歷史敍事法來削減規範倫理,這是他的德性論的特點,因此被看作是後現代的。但德性論也沒有解釋人爲什麽要追隨德性,他只是用歷史的角度考察德性是什麽概念,是怎麽發展的,有什麽作用等,只是一種歷史描述,缺乏反思意識,也沒有對人的道德做理論上的反思,不能稱之爲道德哲學。西方學者的補救不是很成功的。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倫理學必須向它的當代形態轉變,只有這樣,才能推進我們的倫理學研究。這個轉變體現于以下幾個範式轉換。
1、抛棄價值和事實的二元對立範式
倫理學屬於人對自身的反思,要從人的存在這個最簡單的事實出發。人究竟是怎樣的存在?達爾文的進化論告訴我們,人的最簡單、最基本、也是最容易忽視的事實就是:人是自然界的物種,人是自然進化的産物,人的存在是經過自然選擇,不斷適應環境的性狀。有人認爲這是一種還原論,即把人的存在還原爲物的存在,其實並非如此;所謂還原論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而從生物的角度考察人的存在,只是強調從一個最簡單的起點出發,一點一點地疊加,一點一點地推進,直到得出一個較爲複雜的結論,這是與還原論根本不同的方向。
如果從人的最基本的存在事實出發,那麽,人和動物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區別。傳統倫理學把人想得太好,認爲人與動物有根本的、不可逾越的界線。孟子的“性善論”特別強調人與禽獸的區別,講道德四端:側隱之心,是非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認爲沒有這“四端”就“非人也”。但是孟子有什麽事實證據呢?很少,他只是舉人們在看到孺子快要掉到井裏時都有“怵惕側隱之心”的例子,來說明人人都有側隱之心。但這個證據能說明問題嗎?我們現在看到是相反的。請看下列新聞媒體公佈的兩則消息。
新華社海口2003年4月4日電(莊斐):3日上午8時40分左右,在海口港新碼頭8號泊位,一輛載有5人的汽車掉進海裏,造成車上4名兒童溺死的慘劇。“我跪下來,抱住他們的腿、拉著他們的手,求求他救救我的孩子。可是,他們都不肯下水救我的孩子。”談到日前在海口港慘劇中死去的孩子,李小英早已泣不成聲。
新華網湖南頻道2003年5月12日電(頻道責編 胡爲):“湖南一男子高樓跳下身亡, 數百名看客竟鼓掌歡呼。”5月9日11時30分左右,有人發現薑某站在二三六地質勘測隊辦公樓6樓樓頂欲跳樓,就興致勃勃地吆喝著在樓下圍觀,一時竟聚集了數百人。中午12時左右,110巡警接到好心群衆報警後,立即趕往現場,並馬上通知了該市消防支隊組織營救。民警和姜的親友上樓與其展開周旋,勸說他放棄輕生念頭,姜一度被勸動情而痛哭流涕。同時,消防官兵迅速確定了一套營救方案,在樓下鋪開了救生氣墊,並準備萬不得已時將其制服。然而,就在此時,樓下圍觀的數百名看客卻不斷發出歡呼聲,有人甚至高喊“快跳啊”,“我都等不及了”……下午2時30分左右,薑某就猛喝一口酒,把酒瓶一甩,縱身躍下了20多米高的樓房。 “砰”的一聲,血流滿地,圍觀人群一陣悸動,隨之竟爆發出熱烈的鼓掌聲與歡呼聲。 一名在現場營救的民警憤怒地質問一旁的看客:“你們怎麽這麽無恥,鼓什麽掌,要不是你們這樣大呼大叫,他是不會這樣跳下來的!”幾分鐘後,突降的傾盆大雨將血污了一地,圍觀人群也迅速散去。
這些事實與孟子所講完全相反。這些人有惻隱之心嗎?沒有!能因此說他們不是人嗎?把“不是人”作爲道德譴責,可以怎麽說,但這並不是說這些人事實上不是人。20世紀60年代開始,有一門新興學科——社會生物學,它探討社會集體的生物學基礎,社會不是人所特有的,動物也有,如螞蟻、蜜蜂,爲什麽螞蟻蜜蜂社會能行成了因爲他也有利他的行爲,動物沒有利他意識,但有利他行爲,這是在自然選擇中保存下來的適應環境的性狀;如果沒有利他行爲,社會就會毀滅,就沒有螞蟻和蜜蜂的種類了。而正是因爲這種群體,才使他們保存不下來。同樣,人類爲什麽有利他行爲?因爲自然選擇,如果沒有利他的道德行爲,人類就沒有社會,就不能生存。這樣看來,動物與人類並無本質區別,都是有社會、有利他習慣的物種。亞裏土多德曾說:“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同時他也說過:“沒有德性的人是最邪惡,最野蠻、最淫蕩,最貪婪的動物”。[1]即使是孟子,他雖然主張人性善,但也承認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從基因學上講,人的基因與大猩猩的基因只相差1%。波普也說:“從阿米巴到愛因斯坦只有一步之差”。當然,這個1%,進化的這一步造成的實際後果是十分巨大的。我們要從進化和自然選擇的觀點出發,來理解人類存在的事實,並進一步解釋人類道德和理性的特徵。
2、從“義”到“利”的範式轉換
西方哲學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概念:奧康剃刀,這就是簡單化原則,要把不必要的假設都剃掉。應用倫理學也要從最簡單的事實出發,儘量少對人性作出太多的假設,而是把利益作爲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國際政治有一條原則:“沒有不變的敵人,也沒有不變的朋友,只有不變的國家利益。”應用倫理學也要承認:“沒有不變的善,也沒有不變的惡,只有不變的利益”。那麽不變的利益是什麽呢?就是更好的生存,這本來是功利主義的基本原則,用利而不是義作爲衡量道德的標準。功利主義剛開始時,被人理解爲抛棄道德,遭到普遍反對。正如現在生物社會學也引起軒然大波,認爲它把人下降爲動物,是對人的褻瀆。功利主義在應付批評時,不斷對“利”的概念做修改,結果是對“利”作了過多的假設。功利主義的集大成者是西季威克,他把情感性的功利主義轉化爲原則性的改良主義,他認爲功利不是個人情感的快樂,而是一種原則。他的《倫理學方法》很複雜,講了不少原則,但歸根到底就是兩條:合理化原則,利益最大化原則;就是說,用合理的手段實現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是道德的本質。[2] 其實問題沒有那麽簡單。正如非理性主義對功利主義提出的挑戰,人的很多行爲、思想都不一定是理性的;人也不一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弗洛伊德就說,人不僅有愛欲,還有死欲;不僅服從快樂原則,還服從毀滅原則。毀滅自己的和別人利益就是所謂“損人不利已”,這樣的事在日常生活中太多了。義和利不是對立的,公與私也不是對立的,它們都是可以互相轉變的。應用倫理學的原則應該遵循從私利到公利,再從公利到公義的路徑。
我以爲,利益、人性和道德構成了一個三角形,每條邊既可以表示符合關係,也可以表示反對關係。如功利論認爲利益與道德之間有符合關係,而目的論和義務論大多(不是全部)認爲兩者是反對關係。再如,性善論認爲人性與道德之間有符合關係,而性惡論者則認爲兩者是反對關係。還比如,經驗主義的倫理學傾向於認爲利益與人性之間有符合關係,而先驗主義的倫理學傾向於強調兩者的反對關係。當然,這些只是大概的傾向,思想史上總是有一些一般的規律、傾向和特徵所不能概括的特例。
研究利益、人性和道德這一“倫理三角形”的目的,不只是爲了概括歷史,更重要的是指導現實。我們所處的現實是現代社會,“現代化”(乃至“全球化”)、“現代主義”(乃至“後現代主義”、“現代性”(乃至“後現代性”),等等新的名詞術語,都是對我們所處的這一現代社會的特徵的概括。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是“多元化”,生活方式、價值判斷、思想方式、國際關係,等等,一切似乎都是多元的,但這一切的“多元化”都是以利益爲軸心,利益多元化是現代社會的最顯著的一個特徵。道德家常用“物欲橫流”來譴責現代社會,但這不能阻止現代社會的利益多元化的潮流。與其憤世嫉俗地譴責社會,不如冷靜地、理性地面對現實,解剖人性,重建道德。
按照以上的構想,“倫理三角形”的“利益”維度應該佔據中心地位。在人性與利益的關係上,現在興起的社會生物學提出了一些新見解。其邏輯是從利益來推斷人性:人類的利益歸根到底是人種的生存和發展,而人性則是自然選擇的産物,是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所必備的。如果沒有“惟利是圖”的人性,也就沒有現實存在的人類,甚至連種種關於高尚人性言談的聲響也不會留下。但是,同樣需要注意的是,與“人性”相符合的“利益”是人類利益,它可以表現爲個體利益,也可以表現爲群體利益。從生物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基因利他主義”和“基因利己主義”對於一個物種的保存是同樣重要的。
在利益與道德關係問題上,進化博弈論用數學模型彌補了功利論的經驗主義。對利益的算計有多種博弈論模式,有些會損害群體利益,甚至導致物種的滅亡;但自然選擇總會保留最佳的利益博弈模式。就人類而言,最佳的利益博弈論模式與道德規則是符合的。
3、從金律、銀律到銅律的轉換
所有的道德律都是價值律,但反之則不然;有些價值律可以是非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價值律是人們選擇取捨可欲事物的準則,不同的準則以對可欲事物價值的不同判斷爲基礎。對可欲事物價值的判斷於是也有高下之分。價值律本身是有價值的。如果用金屬的價值來類比,我們可以把價值律分爲“金律”、“銀律”、“銅律”和“鐵律”這樣四個由高到低的類別。
在這四類價值律中,“金律”和“銀律”是道德律;“銅律”本身是非道德的,通過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等各方面的道德導向,它可以産生合乎道德的社會後果;但如果沒有這些方面的道德導向,非道德的“銅律”就會淪爲反道德的“鐵律”。
《論語》說:“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耶穌基督說:“你要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怎樣對待別人”。這是倫理學的“金律”的標準表達。金律就是“欲人施之於己,亦施之於人”,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銀律”。“金律”和“銀律”不只是同一個道德律的肯定和否定兩個方面,而且是這一道德要求的高低兩個層次,“金律”的肯定性要求比“銀律”的否定性要求更高,因而有更大的倫理價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要求人們不加害於人,不做壞事;“欲人施諸己,亦施於人”進一步要求人們盡己爲人,只做好事。“不做壞事”與“只做好事”,“避惡”與“行善”不是同一行爲的兩個方面,而是兩個層次上的對應行爲。“不做壞事”是消極的,被動的;“做好事”是積極的,主動的。“不損人”相對容易,“利人”則比較難,“專門利人”最難。
簡單地說,“人施於己,反施於人”,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怎樣對待別人,這就是“銅律”要求人們根據他人對自己的行爲來決定對待他人的行爲。一些行動準則,如“以德報德,以怨報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血還血,以命抵命”,等等,都是“銅律”的具體主張。
“銅律”不要求對人性的善惡作出先驗的預設,但要求對他人行爲的好壞作出經驗判斷;並且,還要對自己對他人所作出的反應所引起的後果作出進一步的判斷,如同下棋一樣,每走一步,要考慮到以後幾步甚至十幾步的連鎖反應。 “銅律”是關於利益和價值的博弈規則,而不是關於道德行爲規則。
與“銅律”密切聯繫的利益博弈蘊涵著基本預設:一是“利益最大化原則”:每一個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二是“理性化原則”:人的理性可以認識什麽是自己的最大利益,並且決定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如果這兩個預設的原則能夠成立,“銅律”就可以導向道德的原則;反之,如果它們不能成立,“銅律”就會導向反道德的“鐵律”。
簡單地說,“鐵律”就是“己所不欲,先施於人”。 “先施於人”的“先”不僅指時間上的先,而且指策劃在先;策劃于對方的報復之先,使對方的報復行爲失效。從而擺脫了“銅律”限制。“先施於人”的策劃與“銅律”所預設的理性的博弈不同,這完全是賭徒式的非理性博弈。賭徒心理的非理性具有冒險性、僥倖心理和一次性心理。冒險的、僥倖的、一次性等非理性的行爲所實現的並不是個人的最大利益,而是自己的和他人的利益的共同毀滅。
希臘神話把人類的歷史分爲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借用這一比喻,我們可以把古代社會比做黃金和白銀的時代,把近代社會比做青銅時代。這一比喻的意義是,古代社會的道德原則是“金律”和“銀律”,近現代社會的社會道德基礎依賴於“銅律”。當代社會既不能返回到黃金和白銀的時代,也不能維持在青銅時代,更不能淪爲讓“鐵律”占主導地位的“黑鐵時代”,只能走向一個“黃銅時代”,即“金律”、“銀律”和“銅律”共同發揮作用的時代。
“黃銅時代”是這樣一種社會環境,它最大限度地保障理性的利益博弈的實施,同時讓賭徒式的非理性博弈失效。“銅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成爲公共利益的道德基礎,並能有效地限制“鐵律”的範圍和作用。“黃銅時代”注意繼承“金律”和“銀律”的道德傳統,使之與“銅律”相適應,把社會公利轉變爲社會公義。社會公義反過來促進了“金律”和“銀律”的實施,形成“銅律”與“金律”、“銀律”之間的良性迴圈。
4、方法論的範式轉換
傳統道德哲學的方法是把人下往往上面拔高,即先建立一個道德形而上學,從最高原則出發,把人的境界往上提升;而應用倫理學的方法正相反,它是把人從低處向高推舉。美國哲學家丹尼特(Daniel Dennett)做過一個比喻,說現代人與傳統人的思路有一個區別,傳統的思路是吊車型(skyhooks)的,現代人的思路是舉重機型(cranes)的。[3]所謂吊車型,就是立足于高處往上拔高,所謂舉重機型,就是立足于低處向上推舉。這個低處,甚至可以低到把人看成動物,然後一步步往上推。這兩條路的結果是殊途同歸,最後都要達到道德境界的目的,但過程是不一樣的,吊車型的思路作起來往往不是很通暢,需要打通很多隔閡關節,做不到徹上徹下;而從低到高的上升路線,因爲不需要太多假設,往往進行的更通暢,更有效。
5、發掘中國倫理傳統的解釋範式的轉換
發展中國的應用倫理學,離不開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資源,詮釋的重點應從儒釋道轉向墨荀韓。儒釋道思想是中國傳統倫理學的主體,它們都有濃厚的“心性”論的色彩。儒家是中國傳統倫理學的主體,佛教談“心”和“性”,到了宋代,理學吸收了佛道教一些因素,發展了一個完整的,道德形而上學的心性學說。
中國傳統文化的資源中墨荀韓這一部分的意義常常被忽視。墨子、荀子、韓非子的思想更適合應用倫理學的基本原則。墨子是一種功利主義學說,主張兼愛,但人爲什麽要兼愛?就是爲了交相利;他也從功利的角度談國家的起源,國家就是爲了不使大家爭鬥,爲了達到大家的利益而建立的公義,這可以說是中國的“社會契約論”。
荀子主張“性惡說”,他所謂的惡其實不過是人的自愛好利、趨樂避苦等非道德本能。非道德並不等於反道德,相反,通過聖人的“化性起僞”,人類被引向禮義社會。“化性起僞”是從非道德的本能走向道德社會的過程,這一過程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利益博弈過程。荀子說,聖人和常人的本性並沒有什麽不同,“君子與小人,其性一也”。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爲什麽與衆人同樣“性惡”的聖人能夠做出創立禮義的善舉呢?荀子回答說,聖人的高明之處在於善於積累人類的經驗智慧,“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積”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善於進行利益的博弈,知道人的長遠利益所在。“積”不同于孔孟所說的“推”。孟子說:“聖人者,善推己及人也。”“推”是類比,“積”是積累;“推”是道德的延伸,“積”是在經驗積累的過程中,進行步驟越來越複雜的利益博弈,達到了對人類的長遠利益的認識。“積”本身是一種非道德的能力,但其結果卻是“聖”。荀子把這一過程刻畫爲:“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從理論上說,每一個人都有成聖的認識能力,“塗之人可以爲禹”。但實際上,“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荀子·性惡》)。常人對利益的博弈局限於個人的暫時利益,眼光短淺,博弈幾招也就罷了,這就是“不可積”。
法家不但講人性是“自利”的,而且提出人的“自利”之心即是“算計之心”。《韓非子·六反》中甚至說:“父母之于子也,猶以算計之心相待也。”君主不應該違反這個事實,而要順應它,這樣才能使利已之心、算計之心爲國家服務。這就是“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道理。(《韓非子·八經》)以上用了幾個例子,爲了說明墨荀法的理論特點,這些特點與應用倫理學方向有一致之處。如果充分發掘了吸收這些傳統的思想資源,中國應用倫理學將會得到更堅實和廣泛的懂得哲學的基礎。
仁道與全球倫理
焦國成
隨著經濟全球化客觀趨勢的加劇,各國、各民族之間政治和文化的互動關係也進一步加強,全球倫理也成爲人們日益關注的話題。來自不同國家、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們雖然都在談論著全球倫理,但對全球倫理的理解卻有著巨大的不同,即使同樣的話語也包含著不同的意義。我這裏所說的全球倫理,也只能是對全球倫理的一種中國式的理解。對於倫理的理解決定著倫理的行爲,倫理理解上的差異常常導致倫理行爲的不諧和衝突。21世紀的人類歷史將怎樣書寫,是用美妙和諧的音符,還是用血與火的文字?從倫理的角度來看,這取決於各個國家和民族對於全球倫理的認同程度。
一、人類的生存: 優勢和危機
人類如何才能活下去、如何持續地活下去的問題,一直伴隨著人類存在的始終。我們知道,在人類幼小的童年,人類在諸種強大的自然力擠迫的夾縫中艱難地生存著。人類的初始,族群內部的團結一致,是人類生存下去的重要保證。荀子曾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之所以能群,在於人通過各種辦法和途徑能使不同的人達到“一”。由於人能“一”能群,所以發展得十分迅速。人類借助于現代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力,由宇宙萬物中之一物發展成爲整個地球的主宰者。
人類在今天已經變得很強大了,強大得已經沒有了天敵。但是,主宰著地球的人類能夠真正地主宰自己嗎?因具理性思維和反思能力而稱雄於地球的人類,如果認真地反思一下這個問題,一定會得出懷疑的結論。
現在的人類,面臨或即將面臨著四大衝突:其一是人類與異己的自然環境和自然力量的衝突;其二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其三是人類個體自身內部的衝突;其四是人類與人類創造物之間的衝突。這三種衝突,既是人類前進的動力所在,也是人類毀滅的根源所在。
人類所面臨的第一種衝突,是從人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存在的。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人類是在大自然的壓迫下生存繁衍的。近代以來,由於人類優越的特質,由於人與人的分工協作,由於人類長期的力量積累,更由於當代科學和文明的進步,人與異己的自然環境和自然力量的每一個衝突大都是以人的勝利而告結束。人類經過長期的進化和發展,便形成了這樣一種人類自身所無法克服的矛盾和衝突:一方面,是人類因爲積古往今來整個人類的智慧和勞動而實際擁有的越來越巨大甚至是無限的能力;另一方面,掌握這種巨大能力的是具有衝動、狂熱、疾妒、仇恨、絕望等情欲、不可克服的自身局限性及由此而形成的短視且只有幾十年壽命的有限個體。我們可以這樣形象地描述這種無限和有限巨大的反差和矛盾:一個未孩的嬰兒,手裏拿著一個威力無窮的魔棒。
當然,人類所取得的勝利並不具有永恒的意義。自然界對於人類的欺淩,總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加以報復。這種報復又迫使人類調整自己的行爲,改進自己的技能,從而變得更加強大。變得更加強大的人類反過來對於自然實施更加粗暴的欺淩,而自然則又給予人類以更加嚴厲的報復。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人與自然之間就是處於這樣一種不斷升級的相互對抗和衝突的惡性循環之中。
人類所面臨的第二種衝突,要比第一種衝突更加險峻,更加難以解決。當今時代,尤其是近百年以來,世界上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階級和不同階層的人們,由於所持的利益不同,所抱的政治信念不同,所守的宗教信仰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好惡和種種偏見;由於這種偏見而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鴻溝,並使彼此陷入了矛盾、對立、衝突和戰爭之中。人類越是強大,這種對立和衝突的後果就越是可怕。這就猶如好多個彼此不和的未孩的嬰兒,每個人手裏都拿著一個威力無窮的魔棒。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加戰爭的國家33個,死傷3000余萬人,捲入戰爭的人口在15億以上。時隔僅20餘年,就爆發了一場更大規模的世界戰爭。在這場長達十來年的世界戰爭中,先後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20多億人口捲入了這場戰爭,就連人類當時所能製造出來的最先進的毀滅性武器都使用上了。這次戰爭結束後,世界局部範圍內的衝突和戰爭,幾乎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當今最典型的表現就是美英和以伊拉克、巴勒斯坦爲代表的阿拉伯世界的對立。
由此可見,隨著人這個“天之驕子”能力的急劇而普遍地增強,人類仍然沒有擺脫一個更爲嚴峻的生存問題。這種生存的威脅不是來自於其他物種的威脅,而是來自於人類內部。以國家、民族之間的衝突和政治、宗教信仰之間的衝突形式爲代表的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當今軍事科技的突飛猛進,使人類愈來愈面臨著同歸於盡的危險。
人類所面臨的第三種衝突,是比第二種衝突更深層次的衝突。道德和利益之間的對峙,理性和欲望雙方的交戰,奮鬥和享受之間的擇取,愛和恨、生和死之間的較量,都是這種衝突的基本內涵。人類就是在不斷的內心矛盾和衝突中走向未來的。在世界範圍內的現代化日益實現的今天,人們心理的煩躁、情緒的不穩、忍耐性的下降、心理的綜合性疲勞、精神的空虛、理想和奮鬥精神的缺失,似乎比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嚴重。人們那種田園式生活方式下的寧靜淡泊的心境已經不再,取而代之的不是激昂的拼搏就是心理上的厭倦和意志上的頹廢。這種內心狀態實際上是現代工業社會所帶來的日益惡化的環境、人際的激烈競爭和衝突、人情的冷漠在人們心理上的反映。人類在當代的內心衝突,極易導致思想行爲的失控。世界現代化進程中造成的人類這種煩躁、厭倦的心理和精神,不能不說給人類未來的前途蒙上了一層重重的陰影。
人類所面臨的第四種衝突是人與自己“創造物”的衝突。異化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人的創造物常常反過來控制和反對人自身。人所創造的産品或物品總是給人帶來不良的影響,廢棄物造成污染給人以損害,高消費品則常常使人懶惰、某些體能下降而對人的創造物本身依賴。更值得憂慮的事,則是人創造的智慧物品與人類的矛盾。未來的高智慧的機器人是不是還“願意”被人所指揮、爲人服務?如果出現因特殊目的“克隆”的特殊人群,他們與原有的人將會發生什麽樣的關係?潛在著的矛盾和衝突的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
從這四個方面來看,如果人們對於自身不加改造,是根本不能主宰自己的。不能自做主宰的人,一定是會不斷幹愚事的。如果說有朝一日人類會毀滅的話,那麽這種毀滅人類的力量一定來自人類自身。
我以爲,人類當務之急並不在於在衆多的發明之上再加上幾個更新的發明,使已經很強大的人類更加強大,而在於糾正人類自身的弱點,克服人類內耗,消解可能導致人類毀滅的自身方面的各種因素。研討建立並推進全球倫理,形成人類共同的行爲標準和道德觀念,和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利益追求的人群之間的關係,加強人類的自控能力,則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二、全球倫理的構建:多元和一元
如何解決這種人類生存危機?中國人曾經想出了許多方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這樣幾種:
第一種,中國道家的解決方式。道家早就看到了人類未來的生存危機,因而反對發展科學技術,反對搞大一統的政治,主張回歸自然,讓人生活在“小國寡民”的原始部落狀態,讓每個人都有強健的身體而沒有強健的意志,鼓腹而遊,渾渾噩噩地生活到老死。這種方式也就是不搞大一統,不提高社會文明。顯然,這是一種消極的方式。它與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相反,靠它不可能真正解決人類內部的衝突。在一定意義上說,主張尊重自然、反對全球化的人都可以算做是道家的追隨者。(1999年,來自世界各地的數萬抗議者圍困、堵截西雅圖世貿組織會議。2000年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開年會,來自歐美各地的數萬名抗議者,包圍了會所,堵斷交通,強烈反對國際金融資本推行全球化的計劃。2001年4月21日,第三屆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美洲國家組織首腦會議,來自美洲國家的大批反對組建自由貿易區的示威群衆頻頻衝突會場。6月15日大批群衆抗議瑞典哥德堡歐盟首腦會議,發生大規模騷亂。僅十天後,近萬示威群衆聚集西班牙巴賽隆納,抗議世界銀行年會在此舉行,並和警方發生衝突,世界銀行被迫取消在此開會的計劃。)
第二種,秦始皇的解決方式。秦始皇以強權暴力橫掃六國,以嚴刑峻法箝制官員百姓,以焚書坑儒統一意識形態,以郡縣制建立大一統的政治。這種方式就是依靠強權暴力,用壓服的辦法消滅矛盾和衝突。這種主張在近現當代也不乏追隨者。(如希特勒法西斯主義者、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奉行就是霸權主義。在今天,小布希對待伊拉克的辦法走的也是這種老路。)有壓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有反侵略。上世紀中葉的世界範圍內的反法西期戰爭,當今恐怖主義襲擊日漸頻繁,都是明證。“以力兼人”的霸道,最好能在21世紀壽終正寢。否則,必然還將引起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種對立如果不斷升格,這個人類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的美麗星球最終可能將不復存在。
第三種,儒家的解決方式。人類早年生活的經驗,告訴人類這樣一個真理:人類的生存,從外在的方面說靠的是自己對外在壓迫力的抗爭,從內在的方面說靠的是人類對於正義的認同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內部關係的和諧一致。在儒家之前,管子曾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卻不以兵車之力。孔子嘗讚揚“如其仁,如其仁” 。儒家繼承並發展了這種解決分歧和矛盾的方式,強調以仁愛彼此相處,把四海之內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和兄弟,彼此尊重,相互幫助,讓人際關係中充滿溫情,讓所有的人都得其所得。這種方式是實行仁道,“以德兼人”。這種“以德兼人”的仁道,出自人類的道德自覺,是人類對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汰、強者存活的自然規律的超越。這種方式是解決人際衝突的最好方式。不同的民族在這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當今存在的各種倫理傳統就是這種努力的有效證明。
美好的世界大同生活,實際上是人類共同的追求。基督教所追求的天堂,佛教所說的西方極樂世界,儒家所謂的大同之世、平治天下,都是對全球化的一種理想式的理解。倫理是人與人交往關係的産物。有什麽樣的人際交往,就會産生什麽樣的倫理。由於當時人類交往範圍的局限,人們還不可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的大同社會,因而基督教、佛教、儒家的追求都帶有濃厚的理想性和宗教性。
二十世紀以來後半葉以來,社會經濟、科技和通訊、交通手段的飛速發展,地球越來越變成了一個“村落” ,從此,世界各民族、國家的命運日益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隨著人們活動範圍的擴大,隨著人群與人群、國家與國家以及不同國家、民族、地區之間的集團和個人的交往日益頻繁,日益形成帶有世界性的共同倫理。然而,世界共同性倫理卻是在陣痛中逐漸形成的。民族之間、國家之間、各種政治集團之間的偏見、歧視、壓迫、侵略、仇恨、暴力等等,從反面刺激了世界共同倫理的誕生。在本世紀前半葉,所有的帝國主義列強都毫無例外地要把自己的倫理觀念當成世界共同倫理強加給其他弱小的民族。時至今日,這種情況仍然是存在的。
九十年代以後,人們已經越來越達成這樣一個共識:如果沒有一種全球性的倫理,也就不可能有美好的全球性的秩序,就不可能有人類美好的未來。因此,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不再只是消極地等待世界共同倫理或普遍倫理的自然形成,而開始以積極的態度去構建它和完善它。1993年9月,世界宗教議會通過了《走向全球倫理宣言》,後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設立了“普遍倫理”專案,並爲人們提供共同討論的機會和勾通國際與政府的講壇。
然而,在我們這個地球上,已經存在著多種倫理,而且這些倫理之間常常還是互相衝突的。這些倫理中哪些是先進的?哪些是落後的或腐朽的?用什麽樣的標準、靠誰來認定?要建立的全球倫理與既存的倫理之間是一種什麽關係?用什麽樣的辦法和途徑來建立全球倫理?靠誰來建立?在這些問題上,人們特別是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們有一個嚴重的誤區,這就是要淘汰那些他們認爲的腐朽、落後的倫理傳統,建設一種先進的、文明的、統一的全球倫理。
倫理是生活和習慣的産物。有什麽樣的生活就會産生什麽樣的生活習慣,有什麽樣的生活習慣就會産生什麽樣的倫理。在我看來,凡是適合一定人群生活習慣的倫理就是好的倫理,不適合這個人群生活習慣的倫理就是不好的倫理。世界上現已存在的各種倫理傳統,就是在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生活習慣中産生的,因而毫無例外地都有其合理性。它們彼此的具體規範之間並不一定具有可比性,儘管一個族群在審視另一個族群的倫理的時候,總是有許多批評的。莊子曾經論述過,人在高高的樹上會膽戰心驚而猿猴卻不會,人在濕泥裏時間長了會感到不適而泥鰍卻不會,這並不是只有人才知道什麽是舒服。人人都知毛嬙、麗姬是美麗的,但鳥見之高飛,魚見之潛底,鹿見之逃跑,這也並非只有人才知道什麽是美。野鴨子腿短,但短得自在;仙鶴的腿長,但長得舒服。兩者不要看著對方不順眼,野鴨子不要想法把仙鶴的長腿截短,仙鶴也不要想法把野鴨的腿續長。這樣一種觀念和方法用在全球倫理問題上,這就是不同文化和倫理傳統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習慣,而不應該強求一律。
在倫理上強求一律至少會産生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消滅多元倫理傳統帶來的問題。世界各族群的人民都是受其倫理傳統觀念影響的人民,讓他們完全抛棄自己的倫理傳統,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而在消滅多元倫理的時候,必然會引起對抗和衝突,導致人際的不和諧。這顯然與建立全球倫理的初衷是南轅北轍的。
其二,選擇一元倫理所遇到的問題。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你認爲好的事物不一定我認爲好,你我都認爲好的事物第三個人不一定認爲好。在倫理問題上也是一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宗教傳統總有不同的倫理觀念和倫理規範;站在不同的宗教傳統和道德傳統中去看一種事物,必將得出不同的結論。如果強勢的一方堅持己見,實行文化和倫理的霸權主義,硬性地統一,必將招致衆多的非議。
其三,建立一元倫理所帶來的問題。傳統是歷史在現實中的延續,傳統既歷史的也是現實的。當今只有那些符合世界各民族的倫理傳統,至少是不與世界各民族的倫理傳統相對立的觀念,才能被這個民族所接受;脫離了倫理傳統就不可能建立起全球共同倫理。即使有一種勢力像一個國家制定一部法律一樣制定出了全球倫理規範,那麽制定出來以後靠什麽來推行?如果靠強勢國家或靠強硬的手段來推行,那麽它就不是全球倫理,而是世界法律,是屬於強勢國家的世界法律。這必將受到弱勢國家的抵制。倫理的運行本來與法律有質的區別,即使勉強建立起來一種被稱之爲“全球倫理”的東西,也不可能真正被世界各國人民所遵行。
其四,倫理一律所帶來的問題。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時候,它的褪化和衰敗也就到來了。因此,多元的倫理是不能消滅的,既沒有必要消滅,也不可能消滅。
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要否認落後的民族倫理傳統改革的必要性,也不是要否認建立一元的全球倫理的必要性。世界歷史在不斷地向前發展,那些愚昧落後、脫離歷史文明大道的倫理傳統終究是要滅亡的。作爲代表人類倫理發展方向的全球共同倫理,也不應該去吸取腐朽的倫理拉圾來充實自己。全球化的現實、人類的全球性活動和生活,都要求建立起進步的、文明的、有利於全球人的、且能爲人類共同遵守的一元的全球倫理。這種一元的全球倫理應該是符合世界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願,不與當今各民族的倫理傳統相脫離,有利於世界各國的交往,有利於人類發展的未來。至於認定的辦法,那就只能通過對話、討論、協商的途徑,用民主的辦法來加以解決。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杜絕任何的強權行爲。
建立全球倫理,只能由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民族根據自己的倫理傳統、根據自己的理解提出全球倫理規範。這樣必然會出現多元或多種理解的“全球倫理”,而在這些“多元全球倫理”中存在著的共同點則可以成爲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倫理。這種多元全球倫理中存在的共同倫理的建立和發展,要由多個國家、多個民族來共同推動。
對於不同的全球倫理的提法,我認爲應該堅持三點:其一,鼓勵和支援。如果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們具有探討和建設全球倫理的興趣,這絕對是一件好事,因爲這對於推動普遍統一的全球倫理的形成有好處的。其二,尊重和寬容。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宗教背景和傳統文化的背景下,而且對問題的理解總會從自己的知識背景和文化背景出發,在這一點上,每一種觀點都值得尊重和寬容。其三,平等交流和對話。只有在交流和對話中才能彼此理解,才能存異求同,互相學習,互相補充,逐漸求得更多的一致性。
這種對待全球倫理態度本身就是一種仁道。仁道也就是人道,是人與人的相處之道。仁道中有一條最基本的規定,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願意別人把某種觀點強加於我,那麽我也就不要把我的觀點強加於人。以仁道行事則順,不以仁道行事則逆,這是歷史教給我們的經驗。
三、仁道的全球倫理:愛人與克己
仁道是由孔子及其儒家提出並加以闡發的,已在中國已經存在了近二千五百年之久,而且經歷代學者的研究和發揮,形成了一個內容豐富的理論系統。關於這一理論本身,這裏無須加以闡述。在這裏,僅就其所內含的全球倫理意義及其人道原則略作說明。
“仁”,在漢字中寫爲“人二”,亦即“人人”,講的就是人類相處之道,可以簡稱爲人道、爲人之道,是關於人類倫理規則、做人的理想及正當途徑總稱。它上于天道相對,下於禽獸之道相對。儒家認爲,人與禽獸不是同類動物,故所遵行的規則不同。禽獸的行爲沒有規則,僅僅受本能和情欲的驅使,過得是一種弱肉強食的生活。人不同於動物,他克制自己的本能和情欲,遵行當然的規則,過一種應當的、文明的生活。從內在含義上說,所謂仁愛也就是對人施好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盡可能地幫助別人,使別人得到好處。實行仁的方法就是“能近取譬”,即推自己的愛父母子女之心而至於天下人,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的道德的實質性含義,也就是讓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得到人道的對待。
儒家在闡發仁道之時,就是從普遍適用的意義上立論的。孟子就曾經祖述過孔子的話:“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他們講仁道,就是在講人與人的相處之道,不僅是古代中國人與中國人的相處之道,也是當今中國人與中國人的相處之道,也是中國人與世界各國人的相處之道,同時也是所有人的相處之道。只要是人,就應該以人的方式相互對待,這可以說是仁道的最抽象的意義。
從全球倫理的意義上講,仁道可以分爲兩個方面:其一是愛人,其二是克己。簡單地說,仁道有幾個要點:
其一,愛人是愛一切人,不論是有權勢地位的“大人”還是沒有權勢地位的“小人”,不論是文明化程度較高的“國人”還是文明化程度較低的“野人”,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不論是中國人還是番邦外國之人。這其中包含著一種不分種族、國別、貧富、衆寡、強弱、智愚、文明與落後,大家人格人一律平等、都應該彼此尊重的思想。
其二,愛是一種惻隱、慈悲、親愛之心,是對人施真正的好心而且不求回報。正像韓非子《解老篇》所說的“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報也”。愛人必尊敬人,愛人必寬容人,愛人必讓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強迫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愛人的方法是“能近取譬”,即以對待自己最親愛、最親近的人爲例子,以這種心對待人。這其中包含著反對侵害人、壓迫人、掠奪人、欺服人的可貴道德主義思想,包含著愛惜生命、消除暴力的和平主義思想。
其三,與人相處不融洽時首先要反省自己的過錯。孔子所說的仁是一種君子之愛。“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意思是說,君子講仁道,當與人産生矛盾之時首先要反省自己、檢討自己,而不是埋怨別人。孟子對其有進一步的解釋:“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治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孟子·離婁上》)有這種自我反省的精神,就可以消除人我的對立了。
仁道強調先人後己,不重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這與西方傳統文化中強調權利形成鮮明的對照;仁道強調尊人卑己,主張弱化自己的意志,不強加於人,這與老子的“弱其志,強其骨”的教導有相通之處。當今世界,正是由於某些人、某些國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別國的利益之上,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才造成了一系列的國際衝突和國際災難。
其四,克制自己的私欲,不任意放行。每一個人都是不完善的,都有自己的局限或缺陷,都有可能産生邪惡。明白了這一點,就能知道對自己克制,對別人寬容。人之過,常常在於以己爲是,以人爲非,是自己之是,非他人之是。如果對己不加克制,必然會犯以己強人、以己損人的錯誤。因而古人強調仁在愛人而不在愛我,雖厚自愛,不得爲仁。
與私相對的是“公忠”。韓非子曾經提出:“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韓非子·五蠹》)“公忠”講的是對於公共利益和整體利益的忠誠。它強調的是個體利益服從於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整個天下利益,強調的是局部利益服從於整體利益,弘揚的是一種爲社會盡責、爲天下盡忠的獻身精神。全球倫理也應該強調這種精神,應該把人類的共同利益看成是最高利益,樹立人類共同利益高於自己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觀念,應該堅決反對那種把自己國家的利益置於人類利益之上、爲了局部利益而犧牲整個人類利益的各種做法。
當然,儒家提出的公忠道德,雖然其基本精神是好的,在歷史上也是起了進步作用的,然而,它也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和糟粕。它與其他重要的道德一樣,是爲統治階級所宣揚和提倡的,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成爲統治階級維護自己統治的一種精神武器。統治階級爲了維護自己的政權,總要把自己說成是國家利益、民衆利益和整個天下利益的代表,甚至把自己的私利說成就是國家利益、民衆利益和天下利益,並要人們都爲此盡忠和獻身。現在,我們應該吸取這種歷史的教訓,要防止某些國家和個人把自己的私利說成是人類的共同利益,並以此爲武器來打擊真正堅持正義的人們。只有分清楚這一點,我們才能不被某些強權國家所愚弄,才能堅持真正的公忠。對於每一個國家的人們來說,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要把天下看作是天下人之天下,而不能要把天下看作是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私有物。對於現代人來說,不論是年長者還是年幼者,都要把天下看成是現在人和未來人共有之天下,而不能看作是現有人之天下。
仁與公忠是相一致的。自私者只爲自己,把自己封閉起來,而把他人排斥在圈子以外。仁愛的道德就是要把個人的小圈子打開,使他人進入自己的圈子,使自己也進入他人的圈子,使人我之間憂患分擔,福樂共用。仁到大處便是公忠。人的道德反映了人之爲人的本質特徵,所以必將伴隨人類的整個歷程。在孔子的時代,仁被看成是人與人相處之道。在當今的時代,它與世界不斷走向開放、走向融合和一體化的趨勢也是完全相適應的,因而仍然是人與人相處之道。不論東方西方,不論種族膚色,不論文明與落後,大家都是人,都應該以仁愛這種人與人相處之道來相互對待。愛人必人我俱立,人我俱成。孔子曾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自己不比任何人有優先權,人我應該擁有共同的幸福,共同的繁榮。
其五,仁道也包含著制惡、除惡在內。孔子曾講“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這種“惡”,不是因爲對方傷害了自己的利益,不是因爲對方與自己信的不同是一種價值觀。惡是因爲其“不仁”。對於以強淩弱、以己害人、破壞人道、損害人類的共同利益的人和事,都應該予以抵制。
其六,仁道還包含著保護環境、愛惜萬物的含義。儒家認爲,人作爲天的産物,在本質上是與天相一致的。因此,人之道與天之道也是相互貫通的。從而對人與天地、自然、萬物之間的倫理關係也提出了解決的合理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一是“與天爲一”,即把自然與人看成一體,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二是“與自然合其序”,即順其自然,按照自然的規律辦事,而不要事事由人來安排;三是“取物以時”,即按時節來取物,而不妨害萬物的正常生長;四是“節用有度”,即物盡其用,反對浪費。
與大自然的關係問題,實際上也就是現在人與未來人的關係問題。這是一個世界各國面共同臨著問題。由於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由於人們的享受觀念,由於人們在許多方面的惡性競賽,致使我們現在生態平衡破壞得很厲害。假如我們還不重視生態的平衡,只管經濟的發展,那麽一百年後怎麽辦?把資源使用完了,把生態破壞得無法恢復了,子孫後代如何生活?只考慮本代人的利益,而不考慮下一代和更遠的後代的利益,是最短視和最自私的行爲。保護我們共同的航船——地球,過一種簡單樸素的生活,節省地球上的資源,乃是人類的共同利益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崇尚消費主義的國家是沒有資格以全球倫理的建立者和推行者自居的。
在仁愛的原則之下,儒家還講了許多配合仁的道德規則。例如:義,或稱正義,一個含義是仁之節度,或者說實行仁、做到公平的具體的適宜的標準;另一個含義是“惡不仁者”,即抵抗和消除不仁之事。禮,乃是接人待物行爲之具體標準和文飾,它內在地包含著分別、尊敬、禮讓、親和四大精神,以約束自己的言行來體現對他人的尊敬。誠信,就是不自欺,亦不欺人,表裏如一,言出而必行,它體現著自己對人的責任。信可以說是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正常關係的基本保證。和,也就是以和爲貴,相互寬容,用說理的辦法來解決爭端,最後達到和諧共處的目的。
中國儒家提出的這些爲人之道和行爲原則,有著永恒適用的價值。儒家講的仁愛,與基督教講的愛有相通之處。儒家講的信義原則,與西方思想家們提出的契約論有相通之處。這方面的思想,也應該成爲全球倫理的一個組成部分。
儒學的現代化與邊緣化
李 宗 桂
當代中國正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邁進。傳統儒學也好,現代儒學也罷,無論其主觀願望如何,要在當代中國社會生存並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與現代化這個時代主題相適應,質言之,就是儒學必須現代化。否則,就將難以爲繼。而要實現儒學的現代化,儒學要加入現代化的進程,就必然面臨邊緣化的命運。這就引出了儒學現代化與邊緣化的論題。就這個論題展開必要的研討,無論對於儒學自身,還是對於當代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都有積極的認識價值和實踐意義。
- 一. 儒學現代化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儒學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價值系統的創造者和體現者。作爲一個整體,它在追求現代化目標的當代中國社會中,已經失去了它在前現代化時期的歷史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講,儒學是與現代化的價值取向格格不入的。但是,從文化的民族性和歷史繼承性的一面來看,作爲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者,作爲中華民族精神的歷史承載者之一,作爲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鍛造者、推動者之一,作爲中華民族文化特質的重要構成之一,儒學在建設現代化社會的今天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換言之,儒學是可以和現代社會相融的,因而也是可以現代化的。
從歷史上看,儒學曾經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進行自我更新。自從先秦時期孔子創立儒學,到五四以後現(當)代新儒學的形成,儒學經歷了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內容和質量方面都産生了重要的變革。先秦時期以孔孟爲代表的原始儒學,以仁爲思想核心,生髮出一整套道德學說和政治理論,爲後來儒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漢代以董仲舒爲代表的新儒學,適應大一統的時代要求,改鑄原始儒學,援陰陽五行思想入儒,並以陰陽五行作爲建構理論體系的基石和方法,同時吸納法家思想,剝取墨家理論,演繹名家精義,借鑒道家觀點,可謂熔鑄諸子而以儒學爲統率,建立起一個以三綱五常爲核心。以天人感應爲特徵。以維護統治者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爲宗旨的新型而又嚴整的價值系統,從而將儒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宋明時期,程朱陸王等理學家總結魏晉隋唐時期儒學發展的經驗教訓,吸收佛教的思想理論,通過理欲之辨,通過道。氣、理、心、性等範疇的展開,建構起自己的本體論學說,彌補了此前儒學在本體論方面的缺陷,發展並完善了儒家思想,奠定了此後數百年的思維方式、價值準則和行爲范式,宋明新儒學成爲儒學發展史上的新高峰。近代以降, 在西力的強烈衝擊下,爲了解除內憂外患,爭取民族獨立,保存民族文化,懷抱深厚憂患意識的儒家知識份子,被迫但卻有意識地學習西方,力圖通過西方文化之“用”而強健中國傳統文化之“體”,在客觀上更新著傳統儒學。特別是“五四”以後,現(當)代新儒學思潮興起,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等人開其端,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繼其後,劉述先、杜維明、蔡仁厚等人承其統,現代新儒家們力主會通中西,中西文化相互學習,用西方文化的方以智撐開中國文化圓而神的智慧,用西方的科學民主充實傳統儒學,達到內聖外王的目標。儘管人們對於現代新儒家們“內聖”開出“新外王”的論說和價值預期有著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此時的儒學已經不是傳統儒學,而是具有“現代”意味的新儒學,則是不爭的事實。可見,儒學在自己的發展歷程中,由先秦原始儒學到漢代新儒學,再到宋明新儒學,最後到現(當)代新儒學,在思想內容、理論特質和價值取向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而我們說儒學是具有自我更新功能的,是能夠與現代化相容以至相融的。
從儒學的特質來看,它也能夠與現代化社會相適應,它自身能夠現代化。儒學的重要特質之一,就是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並能夠與時俱進。孔子被稱爲“聖之時者”,孔子曾經宣稱“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儒家經典主張“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宋儒倡揚民胞物與,以及上述儒學在不同歷史時期能夠調整、更新自身的事實等,都是儒學能夠包容不同成分、能夠與時俱進的體現。而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後能夠與儒學和平共處,以及宋儒爲創建理學體系而吸收道教和佛教理論等史實,都表明了儒學的包容性和適應性。
從近年現(當)代新儒家學者的諸多學術表現來看,儒學也能適應現代社會,自身也能現代化。現(當)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劉述先、杜維明、蔡仁厚等人,以及他們影響下的現代新儒學的認同者、傳播者,儘管其學術立場、方法、觀點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對於現代民主政治和科學精神的認同卻是一致的,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認同的,而且是積極推動的。甚至,對於五四精神也是肯定的。即使是復興儒學、力圖實現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努力,實際上也蘊涵著現代化的用心。
由上可見,儒學的現代化具備其主客觀的、歷史和現實的可能性,而不是像某些論者所認爲的那樣,儒學只是一具思想僵屍而已。
儒學作爲民族文化的重要構成,不僅具有現代化的可能性,而且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必要性。這個必要性,不僅在於儒學是我們今天建設現代化社會的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更在於儒學現代化本身所面臨、所要解決的諸多問題。簡言之,就是儒學的現代化究竟要化什麽?怎樣化?只有恰當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合乎理性地將儒學現代化的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給儒學現代化的必要性以合理的說明。
在我看來,儒學現代化要面對、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勇敢地化自身,二是執著地化社會,三是堅韌地化現代。
儒學要現代化,首先要從自身做起。要勇敢地丟掉傳統儒學和現(當)代儒學中不適合現代化要求的形式和內容,特別是不符合現代化精神的某些價值期望。例如,要改變唯我獨尊的思想,承認西學、馬列與自己的並存,而且二者具有強大的力量,應當與之平等交流和對話,爭取最終做到三者的良性互動,而不要奢望改變甚至消解二者。又如,要甘於寂寞,甘做“寂寞的新儒家”,踏踏實實做點提升中華民族精神生命的人文精神重建的工作,而不要奢望成爲官學,成爲官方意識形態。再如,要改變思維方式,不要奢望成爲帝王師,不要隨時準備“應帝王”,而要在積極參與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注意把握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提升自身的學術品位,保持必要的距離感和應有的批判精神。
儒學要現代化,還得自覺而又積極地投身現代化事業之中,努力去化社會,去鑄造新的安身立命之道,去淨化社會空氣。儒學的長處之一,是有很強的能動性,有很強的參與意識。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昔日儒家所標榜的志向,在現代化建設的今天看來,未免過於理想甚至過於自負,但用人文化成社會,用君子儒的價值理想和行爲實踐來引導社會向善,應當是可以達到的比較現實的目標。
儒學要現代化,應當在自身逐步現代化的過程中,去化現代。這個化現代的化,不是消解,不是融化,不是將現代化的進程逆轉,而是用儒家價值理想的合理成分去化解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比如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極端個人主義之類。總之,用儒學的合理成分去感化社會,引導社會,昇華社會。
如果現代新儒家以及儒學價值觀的認同者們能夠做到上述方面,則儒學的現代化不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極大的現實性;進而,儒學現代化的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 二. 儒學邊緣化的必然性
怪異的是,儒學在其現代化的過程中,面臨邊緣化的危機。
從邏輯和學理上講,儒學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步邊緣化,具有必然性。現代化的實質是工業化,是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的工業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在這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從文化的層面看,現代化又主要是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過程,是一種全面的理性發展過程。現代化不僅是經濟發展,而且也是政治發展、文化發展和精神發展(參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16頁)。質言之,現代化應當包括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亦即現代化關鍵在於人的現代化,而不只是器物、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從文化的時代性的層面考察,儒學屬於前現代化時代亦即農業社會的産物,它所反映的是古典精神,是農民意識。因此,在以工業文明爲追求的現代化時期,儒學不可能仍然佔據社會主流的地位,不可能成爲社會價值系統的標杆,而只能退居邊緣。
其實,儒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漸邊緣化,有著客觀的理據。我們知道,現代化是以市場經濟爲導向的。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要按照價值規律辦事,以經濟效益爲中心。而儒學的價值取向正好與此相反。儒學所推崇的,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類的道德理想主義。君子恥言利,是農業社會的通則。市場經濟講究競爭,追求效率,“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是最爲生動的詮釋。儒學講求和諧,以犧牲效率、犧牲社會進步爲代價換取社會的所謂祥和之氣。現代社會重視誠信,契約觀念深入人心;而儒學雖然也講究誠信,但重視的是君子一諾千金,而絕無契約觀念。儒學這些與現代化相悖反的意識,必然被社會拒斥,從而必然導致其邊緣化。
從現實政治的運作實際來考察,儒學的邊緣化也是不爭的事實。現時兩岸四地的華人政權,儘管各自依託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架構不同,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儒學不是官方的意識形態,不是指導社會生活的主流文化,這就必然導致儒學的邊緣化。
從學術實踐的層面看,儒學的邊緣化也已是客觀的事實。近年來頗爲引人矚目、發展迅速並且影響甚大的現(當)代新儒學,不僅遠遠沒有落實到社會政治實踐的層面,甚至連在學術界的認同也頗爲有限。“寂寞的新儒家”,一句話道出了儒學復興論者的多少悲涼!在現代新儒學的基地臺灣,儒學不過是各種各樣喧囂聲音中的微弱呼喚而已。在世界漢學研究重鎮的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現(當)代新儒家第三代傳人杜維明先生,爲儒學的第三期發展耗費大量心血,並大力培養儒學後起之秀,希望通過波士頓儒家、臺北儒家、巴黎儒家、東京儒家的培植和共同努力,最終回歸大陸,實現儒學的理想。應該說,杜維明先生的理想甚高,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是,衆所周知,現實的情況遠比理想要嚴峻得多。儒學的邊緣化決非良好的主管願望就能改變。
儒學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邊緣化,我們還可從歷史中得到說明。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中國社會越是現代化,儒學就越是邊緣化,其邊緣化具有必然性。張之洞、曾國藩、李鴻章之類的大儒,儘管對儒學矢志不渝,但他們所奉行的中體西用的政治主張、思想路線和學術觀點,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官方將儒學邊緣化的歷史進程。改良派戊戍變法維新的思想實質,是要變封建階級之法,維資產階級之新,這已使得作爲官方意識形態的傳統儒學在制度的層面遭到致命的打擊。而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奉行的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和政權架構,這更是將儒學從社會生活的中心驅向邊緣。“五四運動”掀起的追求科學民主、打倒孔家店的狂飆,則更是給儒學以毀滅性的打擊,儒學的邊緣化已經成爲定局。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由於政治層面意識形態的原因,儒學的邊緣化自不待言。而綜觀近代以來的歷史,可以說,中國社會是在現代化的軌道上前進。儘管這種前進十分辛酸坎坷,但畢竟是在前進。與這種前進相反的是,曾經長期成爲社會生活中心、掌握著各方面話語權的儒學,卻逐漸地邊緣化了。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頭三十年,是受到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宰製,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取代了傳統中國的儒學意識形態,從而導致儒學的極度邊緣化的話;那麽,上個世紀的後二十年,則是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之風的吹襲下,儒學被刮到了社會生活的邊緣。值得現代新儒家們慶倖的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儒學的邊緣化,與“革命和專政”條件下的邊緣化,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革命和專政”條件下的儒學,被當作“污泥濁水”蕩滌,不僅喪失了往昔獨尊時期的神氣,而且甚至連邊緣的位置都已不保。而改革開放時期的儒學,由於環境的相對寬鬆,文化多元化、價值多元化的出現,不僅“邊緣”的地位日益鞏固,甚至還有向“中心”挪步—-以“邊緣爲中心”的意圖。儒家學者甚至在公開的學術會議上號召發表新儒家的“第二次文化宣言”。這表明,改革開放的二十年來,儒學確實邊緣化並且已經邊緣化了。
今天的世界,是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已經成爲事實。儒學的價值理想要想得以實現,必須有一個載體。這個載體可以是一個政權,也可以是一個群體(階層)。縱觀全球,有哪個國家是以儒學爲意識形態立國呢?有哪個國家中有一個群體(階層)在躬行實踐,以儒學的價值取向爲人生的歸依呢?缺乏載體的理想,僅僅是理想而已!兩岸四地,大陸實行的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儒學無法成爲中心;臺灣、香港、澳門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儒學照樣無法成爲中心。因此,儒學的邊緣化就成了勢所必然。
- 三. 儒學現代化與邊緣化的張力及其功能
從上文可以看出,儒學現代化與邊緣化成爲一個難解的結。社會越現代化,儒學越邊緣化;儒學越將自身現代化,就越將自身邊緣化。這種悖反的悲情狀況,可能在某些儒家學者看來是令人沮喪的,甚至認爲是不合天理的。曾有臺灣學者慷慨呼喊:天下不歸於儒,天理何在?就是明證。不過,在我看來,儒家學者也罷,認同儒學的人士也罷,大可不必把儒學的邊緣化看得過分嚴重,應當調整心態,以平常心看待儒學的邊緣化問題。
毫無疑問,在儒學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儒學邊緣化無可避免。重要的問題,並不是去設法使得儒學由邊緣成爲中心,而是在現代化與邊緣化的兩難境地中保持適度的張力,從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弘揚儒學,在實現儒學的現代化的過程中,保持儒學的邊緣地位,使其不致於被現代化的浪潮所淹沒。
古人雲:平常心是道。經歷了兩千年獨尊的儒學,從思想文化的權力的寶座上跌落下來,的確令人感到沈重、失落。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從社會發展的邏輯進程來審視,從建設文明、富強、民主的現代化國家著眼,則儒學的邊緣化是應當而且可以接受的事實。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儒學所依存的政治結構、價值體系、社會心理、經濟基礎等,早已崩解。儒學早已被捲入中國現代化的狂潮之中。既然如此,又何必非要回到以儒學爲中心的“場景”中去呢?失去政治庇護和惡意粉飾的儒學,可能更爲純粹,更爲理性,更符合當代人的精神需要。不爲物喜,不以己悲,從容中道,默默耕耘,最終會結出豐碩的果實。
在邊緣化的時候,儒學應當以當年孔子弘揚仁學的堅韌精神,積極參與到現代化建設之中。在符合價值理性的前提下,認同意識、參與意識的發揚光大,與批判意識、距離意識的始終保持,可以並行不悖。在現代化條件下,參與意識是基本要求。有參與意識,才不致與社會疏離,從而獲得社會的理解乃至認同,保持自身的生命力,發展。壯大自身。可以說,認同意識、參與意識與批判意識、距離意識的統一,才是現代儒家真精神的顯現。由於邊緣化,而使得儒家反省自身,保持距離意識;由於有距離意識,從而能夠保持批判精神。張弛有致,揮灑自如,這才是至高的境界。
儒學作爲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分,有其存在、發展的歷史合理性和現實的需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己正人成己成物,這些閃爍著人類認識真理光芒的思想,不僅在傳統中國它是民族精神的體現,而且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當代中國,它也是合乎人類文明發展方向。體現中華民族偉大智慧的思想。甚至,我們可以說,它的確可以成爲人類正在追尋的普遍倫理的基本要素。儒學應當弘揚的是這種堂堂正正做人的真精神。這樣,無論如何現代化,儒學都有自己應有的地位。
現代新儒家的易學思想論綱
郭齊勇
內容提要 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特重《易傳》,他們借助於詮釋《易傳》來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熊十力的易學是以“乾元”爲中心的本體—宇宙論;馬一浮的易學是以“性理”爲中心的本體—工夫論;方東美的易學是以“生生”爲中心的形上學;牟宗三的易學是以“窮神知化”爲中心的道德形上學;唐君毅的易學是以“神明之知”爲中心的天人內外相生相涵的圓教。他們以現代哲學的觀念與問題意識重點闡發了《周易》哲學的宇宙論、本體論、生命論、人性論、境界論、價值論及其間的聯繫,肯定了中國哲學之不同於西方哲學的特性是生機的自然觀,整體和諧觀,自然宇宙和事實世界涵有價值的觀念,至美至善的追求,生命的學問和內在性的體驗。他們重建了本體論和宇宙論,證成了超越性與內在性的貫通及天與人合德的意義。
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都十分重視《周易》經傳,特別是《易傳》,將其作爲自己重要的精神資源,予以創造性的詮釋與轉化。大體上,他們是沿著宋代易學家的理路講,又在現代所接受到的西方哲學影響下,從形上學、本體論、宇宙論、價值論、方法論的視域來重新解讀易學,開出了新的生面。
一、熊十力:以“乾元”爲中心的本體—宇宙論
關於熊十力的易學觀,我曾在《熊十力思想研究》一書中有專章(第六章)論述。[i]熊先生的易學思想主要源于王弼的體用觀、程伊川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說及王船山的《周易內傳》、《周易外傳》。熊先生自謂根據於且通之于《周易》的“平生之學”的核心,是與船山相通的“尊生而不可溺寂”(或“尊生以箴寂滅”)、“彰有而不可耽空”(或“明有以反空無”)、“健動而不可頹廢”(或“主動以起頹廢”)、“率性而無事絕欲”(或“率性以一性欲”)。他有取于船山易學的活潑新創、力求實用,但又批評船山之“乾坤並建”有二元論之嫌。(其實船山並無二元論,當另說。)
熊先生說他自己四十歲左右“舍佛而學《易》”或“舍佛歸易”,其重心是“體用不二”的本體論。他所提倡的《周易》智慧,是以西學與佛學爲參照的,即不把形上與形下、本體與現象剖作兩片、兩界的智慧。其“真元”“本體”就是“乾知大始”的本心,以“乾元性體”爲天地萬物、現象世界的本體,是萬化之大原,萬有之根基,具足萬理又明覺無妄。
此體即“仁體”。他以“生生”講“仁”。“乾”、“仁”都是生德,是生命本體。他說:“生命一詞,雖以名辟,亦即爲本體之名。……夫生命雲者,恒創恒新之謂生,自本自根之謂命。”“本體是生生化化流行不息的,儒家《大易》特別在此處發揮。”[ii]他把《易傳》生生不已、健動不息的創造性、創新性思想發揮到極致
熊先生認爲,宇宙間有“剛健、純淨、升進、虛寂、靈明及凡萬德具備的一種勢用,即所謂辟者,與翕俱顯,於以默運乎翕之中,而包涵無外。《易》於乾元言統天,亦此義也。乾元,陽也,即辟也……辟之勢用,實乃控禦諸天體,故言統天。……翕不礙辟也,由坎而離,則知天化終不爽其貞常。而險陷乃生命之所必經,益以見生命固具剛健、升進等等盛德,畢竟能轉物而不至物化,畢竟不舍自性,此所以成其貞常也。”[iii]
在熊先生看來,本體之爲本體,是內在的有一種生命精神,或曰心,或曰辟,具有生生不已、創進不息的力量,能成就整個世界(宇宙)。他借批評船山易學而發揮了一套生命創進的理論,指出世界(宇宙)的形成與演進並無目的性,不是有上帝或人有意計度、預先計劃、預定,當然也不是盲目的衝動,只是生命精神的唯變所適、隨緣作主。正因爲有隨緣作主的明智,物化過程是剛健精神的實現過程,而不是迷暗勢力的衝動過程。他借詮釋《坎》《離》二卦,表明生命跳出物質障錮之險陷,而得自遂。在這個意義上,他講精神本體生命的“舉體即攝用”,“即用而顯體”,講“生即是命”,“命即是生”。本體有很多潛能,無窮無盡的可能,原因乃在於本體生命的本質是創造變化,這就是乾陽之性,可以由潛而顯,化幾通暢,現爲大用。
熊先生又用華嚴宗的“海漚不二”與《易緯•乾鑿度》的“變易”“不易”來比喻本體與現象、本體與功能的關係。隱微的常體內具有完備的品質,涵蓋了衆多的道理,能夠展現爲大用流行,使現象界開顯。本體與功用、現象,變易與不易,海水與衆漚是相即不離的關係。
熊反對在太極、太易、乾元的頭上安頭。“乾元性海”可以開發、轉化爲萬事萬物,又不離開現象界。乾元本體統攝乾坤、神器、天人、物我。
其本體論是本體—宇宙論,“體用不二”包容了“翕辟成變”。這一講法源于嚴複的《天演論》。翕辟是乾元仁體的兩大勢用,翕是攝聚成物的能力,辟是與翕同時而起的剛健的勢用,兩者相反相成。此即稱體起用,攝用歸體。熊先生之晚年定論《乾坤衍》直接以乾坤代翕辟。他視宇宙天體、動植物、人類及人類的心靈的發展,每一剎那,滅故生新,是無窮的過程,無有一瞬一息不疾趨未來。他認爲發展總是全體的、整體的發展。他又認爲宇宙之大變化根源在乾元內部含藏的相反的兩種功能、勢用,相交互補互動。乾坤並非兩物,只是兩種生命力,獨陽不變,孤陰不化,變必有對。這些看法與宋代易學十分契合。
熊先生依據《周易》講了一套宇宙論與人生論,此即乾元性體的即體即用、即存有即活動的開顯。無其體即無其用,無其用亦無其體。用是現實層面的撐開、變現、轉化,體是吾與天地萬物渾然同體之真性,是創造性的生命精神,是內在的、能與天地萬物相互溝通、交融的靈明覺知。只有道德的人才能性靈髮露,良知顯現,盡人道而完成天道。
其體用、天人之學又發展爲“性修不二”的功夫論與“內聖外王”的政治觀。就外王學而言,他講庶民政治,講革命,且拿“群龍無首”喻民主政治。
二、馬一浮:以“性理”爲中心的本體—工夫論
馬先生的易學思想帶有很深的理學、佛學的印痕。他抓住的核心是“窮理盡性至命”,“順性命之理”。其易學思想包括以下內容:
首先,將天下學術、天下之道歸於六藝,而六經之教、六藝之道歸之于《易經》之教、之道。他說:“《易》爲六藝之原,亦爲六藝之歸。《乾》、《坤》開物,六子成務,六藝之道,效天法地,所以成身。‘以通天下之志’,《詩》、《書》是也;‘以定天下之業’,《禮》、《樂》是也;‘以斷天下之疑’,《易》、《春秋》是也。冒者,覆也。如天之無不覆幬,即攝無不盡之意。知《易》‘冒天下之道’,即知六藝冒天下之道,‘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故謂六藝之教,終於易也。”[iv] 他又用華嚴宗一攝一切,一切攝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中有一切,一切中有一,交參全遍,圓融無礙的思想,說明《詩》《書》《禮》《樂》《春秋》之教體者,莫非《易》也。
其次,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和“順性命之理”爲易經、易教之主旨。他說:三材之道所以立者,即是順性命之理也。儒者不明性命之理,決不能通六藝。他以“性”“理”思想來說明六經,特別是《易經》。他說:“學《易》之要,觀象而已;觀象之要,求之十翼而已。孔子晚而系《易》,十翼之文幸未失墜,其辭甚約,而其旨甚明。”[v]在概述了漢、宋、清代易學之後,馬先生特別指出:“近人惡言義理,將‘窮理盡性’之說爲虛誕乎?何其若是之紛紛也?…不有十翼,《易》其終爲蔔筮之書乎?”[vi] 他以爲要重視象,重視辭,通過“象”以盡其意,通過“辭”以明其吉凶,不能隨便說“忘象”、“忘言”。他說:“尋言以觀象而象可得也,尋象以觀意而意可盡也。數猶象也,象即理也,從其所言之異則有之。若曰可遺,何謂‘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邪?與其求之後儒,何如直探之十翼?”[vii] 他又說,像是能詮,意是所詮。數在象後,理在象先。離理無以爲象,離象無以爲數。又說:物之象即心之象也。又說:今治《易》者,只在卦象上著例,不求聖人之意,卦象便成無用。
馬先生指出:“聖人作《易》,乃是稱性稱理。”“三材之道所以立者,即是順性命之理也。凡言理,與道有微顯之別。理本寂然,但可冥證,道則著察見之流行。就流行言,則曰三材;就本寂言,唯是一理。性命亦渾言不別,析言則別。性唯是理,命則兼氣。理本純全,氣有偏駁,故性無際畔,命有終始。然有是氣則必有是理,故命亦以理言也。順此性命之理,乃道之所以行。不言行而言立者,立而後能行也。順理則率性之謂也,立道即至命之謂也,故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易》之所爲作也。知聖人作《易》之旨如此,然後乃可以言學《易》之道。”[viii]
以上對理與道、性與命的詮釋,運用了理學家理氣關係的模型。“理”、“性”爲本體,“道”爲流行,命則兼氣。他又說乾元是性,坤元是命,合德曰人。資始者理,資生者氣,總爲一理。又說理必順性命故,離性命無以爲理故。但這個“理”並不在吾人之外,不可用客觀方法求之於外,不能用分析、計算、比較、推理的方式求得,只能由自己會悟、證悟。因此,在一定意義上,馬一浮先生的“理”即是“心”。
與熊十力類似,馬一浮最終把性命之理視爲本心,以心遍攝一切法,心即是一切法。三材之道只是顯本心本體之大用。聖人作《易》垂教,只是要人識得本心。本心與習心不同,我們不能只隨順習氣,失墜本心。
由本體論進入工夫論、修養論,馬先生講“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乾坤合德,故“性修不二”。在性德與修德的關係上,“因修以顯性,不執性以廢修。” 他亦講成己,成物,認爲成物是性份內事,但物之氣有不齊,不得不謂之命,聖人盡性至命,所以知其不可而爲之。在他看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兼性、修而言,兼內聖外王而言;極深研幾,即所以崇德廣業,開物成務;此即成性、成能、成位。
在體用,性修關係上,熊馬有一致性。如對“神無方易無體”、“精義入神”、“各正性命”等的解釋,如關於從體起用、攝用歸體、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的解釋等。但馬先生多用佛學來談,如佛之三身,圓伊三點等,熊先生則不然。熊馬二人無疑接著宋明諸家而討論易學,重心在本體論。馬的講法更傳統一些,熊用了一些現代哲學的講法。熊著意於本體─宇宙論,馬著意於本體─工夫論。
三、方東美:以“生生”爲中心的形上學
方先生很重視《易》的邏輯問題,他評論了京房、荀爽、虞翻等漢易諸家,認爲最重要的是旁通之說,但“旁通之理應當從卦象去求,不應當從易辭去求……應當由易之取象演卦著手,然後再從卦與卦間的邏輯關係,試求通辭”[ix]。他自己曾以現代邏輯手段說明六十四卦的聯繫。
方東美先生的《原始儒家道家哲學》一書,有專章“原始儒家思想–《易經》部分”。他考察了《易》的邏輯及其符號系統的起源與結構,肯定了從符號到道德的轉化。方先生認爲,《周易》符號和卦爻辭系統是從遠古到成周時代的歷史産品,後經周公、孔子的詮釋,成爲人本主義的思想體系,有了道德理性的提升,既保留了原始宗教價值,又轉化爲道德價值,把神聖世界與現實世界聯繫起來,成就一人類的生命道德秩序。方先生指出,《周易》只是經孔子、孔孟弟子的系統研究,對這些歷史資料以哲學的解釋,然後才有了真正的哲學。
方先生強調的是,孔子演《易》之“元德”、“元理”是中國文化精神的主脈,是中國智慧的精品。與熊十力、馬一浮二先生一樣,方先生也肯定孔子對《易傳》十翼的創制,甚至認爲孔子真正的貢獻在《易》。他進而指出,通過孔子與子思,孟子才是真正透悟《周易》精神的大師,貫通《易》、《庸》,從一切生命的觀點、價值的理想、哲學的樞紐上安排人的地位與尊嚴。
方先生所謂“元德”、“元理”,即是“生生之德”,“生生不已”的天地精神。天道的創新精神轉化爲人性內在的創造性,轉化爲人文主義的價值系統。在這裏,“乾元”是“大生之德”,“坤元”是“廣生之德”,“天”的生命與“地”的生命合併起來,是一個廣大悉備的天地生生之德,即創造性的力量,而人處在天地之間成爲天地的樞紐。《周易》是以生命爲中心、以價值爲中心的哲學體系。[x]
方東美先生對《易傳》的解釋,認爲這是中國獨有的“宇宙—本體論”和“價值中心的本體論”。請注意,方先生的講法與熊先生不同,熊先生講的是“本體—宇宙論”,而方先生是從宇宙論到本體論再到價值論的理路。
方先生在《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人》一文中認爲:“《易經》一書是一部體大思精而又顛撲不破的歷史文獻,其中含有:(1)一套歷史發展的格式,其構造雖極複雜,但層次卻有條不紊。(2)一套完整的卦爻符號系統,其推演步驟悉依邏輯謹嚴法則;(3)一套文辭的組合,憑藉其語法交錯連緜的應用,可以發抉卦爻間彼此意義之銜接貫串處。此三者乃是一種‘時間論’之序曲或導論,從而引伸出一套形上學原理,藉以解釋宇宙秩序。”[xi]他又指出:“《周易》這部革命哲學,啓自孔子……其要義可自四方面言:(1)主張‘萬有含生論’之新自然觀,視全自然界爲宇宙生命之洪流所彌漫貫注。自然本身即是大生機,其蓬勃生氣,盎然充滿,創造前進,生生不已;宇宙萬有,秉性而生,複又參贊化育,適以圓成性體之大全。(2)提倡‘性善論’之人性觀,發揮人性中之美善諸秉彜,使善與美俱,相得益彰,以‘盡善盡美’爲人格發展之極致,唯人爲能實現此種最高的理想。(3)形成一套‘價值總論’,將流衍于全宇宙中之各種相對性的差別價值,使之含章定位,一一統攝於‘至善’。最後,(4)形成一套‘價值中心觀’之本體論,以肯定性體實有之全體大用。”[xii]
方東美概括的《周易》的這四點要義,確有見地。他闡發了《周易》哲學的宇宙自然觀、人性論、境界論、價值論,特別指出這幾者的合一。他指出儒家是“時際人”,而“時間”的觀念在《周易》中特別明顯。
就《周易》的宇宙自然觀而言,他認爲《易傳》揭示的是“萬有含生論”,是自然和諧的化育生機論。此由孔子創發,見之於《象傳》、《系辭傳》及《說卦傳》前兩部分。方東美認爲,《周易》生生之理中,育種成性、開物成務、創進不息、變化通幾、綿延不朽諸義,均值得深究。[xiii]方先生指出,中國人喜歡用“自然”代替“宇宙”。中國人心目中的“自然”(宇宙)與西方人不同,不是物質的、機械運動的,不是可以被宰割(或征服)的經驗物件物,而是整體存在界的生存處所,也是萬事萬物順其自然的律則律動變化的過程,是萬物融通爲一的境界。方東美對《易傳》宇宙自然觀的詮釋,肯定其中蘊藏的生機活潑的生命力。他認爲,我們的宇宙是生生不已、新新相續的創造領域。任何生命的衝動,都無滅絕的危險;任何生命的希望,都有滿足的可能;任何生命的理想,都有實現的必要。“保合太和,各正性命”,真是我的宇宙的全體氣象。這一“宇宙含生論”或“宇宙有生論”,確乎是《周易》哲學所代表的中國哲學的特質。他認爲《易緯•乾鑿度》也代表了中國哲學的機體主義的特徵。所謂中國哲學的機體主義,即否定人與物、主觀與客觀的絕對對待,否定世界的機械秩序和由一些元素構成,否認將變動不居的宇宙本身壓縮成一套緊密的封閉系統。這是針對西方哲學而言的。[xiv]
就《周易》的人性論和境界論而言,方先生認爲,據萬物含生論之自然觀而深心體會之,油然而興,成就人性內具道德價值之使命感,發揮人性中之美善品質,.實現盡善盡美的最高之人格理想,惟人爲能。方先生指出,這一意義也是孔子首先創發,見於《乾》、《坤》二卦的《文言》,特別是《象傳》曾系統發揮了這一思想。《周易》講“精進”,“自強不息”,剛健創新不守其故,生意盎然,生機洋溢,生命充實。宇宙大生命與吾人生命徹上徹下、徹裏徹外、徹頭徹尾,無不洋溢著生機活力,生香活意。人的德性生命、價值理想隨之精進而提升。方先生發揮“易簡之善配至德”,認爲在整體存在界的一切人,都是透過生命的實踐來達到至善的境界的。當人們憑藉其創造生機臻入完美境界,就可以與天地合其德,與神性同其工。這即是理想的精神人格,儒家所謂之“聖人”,盡性踐形,止於至善。方先生在解釋《文言傳》時,強調天人合德的至善之境,即爲大人、聖人的最高境界。
就《周易》哲學的價值論、境界論與自然觀、人性論的關係而言,方東美指出,在中國哲學家看來,自然是宇宙普遍生命大化流行的境域,它本身充滿著無窮無盡的大生機。人與自然之間沒有任何間隔,因爲人的生命與宇宙生命是融爲一體的。自然是一和諧的體系,它憑藉著神奇的創造力(所謂鬼斧神工、神妙不測),點化了呆滯的物性,陶冶人的性情,提升人的美德。天德施生,地德生化,生生不已,浩瀚無涯。大化流行的生命景象,不是與人了無相涉的。正因爲人參與了永恒無限的創化歷程,並逐漸地在這一“健動”的歷程中取得了中樞的地位,因而個體生命與宇宙生命一樣,具有了無限的價值和意義。我們面對著一個創造的宇宙,我們每個人只有同樣富有創造精神,才能德配天地。所以,儒家動態流衍的宇宙觀,也就是價值中心的本體論,其基點是哲學人類學的。
方先生論《易》,大氣磅礡,汪洋恣肆,橫貫中西古今,是現代哲學的詮釋,已超越漢宋易學的分別。他的義理,較之熊、馬,更無拘束。
四、牟宗三:從自然哲學到道德形上學
牟先生早年以希臘哲學的形上學、自然本體論來講中國哲學,特別是用新實在論與數理邏輯來討論《周易》,重視漢代、清代易學。他早年認爲《周易》有四個涵意:第一是數學物理的世界觀,即生生條理的世界觀;第二是數理邏輯的方法論,即以符號表像世界的“命題邏輯”;第三是實在論的知識論,即以彖象來界說或類推卦象所表像的世界之性德的知識論;第四是實在論的價值觀,即由緣象之所定所示而昭示出的倫理意謂。[xv]
第一、早期的易學觀─對漢易象數的研究
他提出了關於爻位的五個根本公理:第一,六爻之位各有所象而成一層級性,是謂“六位”公理;第二,六位分爲上中下即象天地人,是爲“三材”公理;第三,二五居卦之中,而爲一卦之焦點或主座,是謂“中”之公理;第四,六爻成爲既濟式者,是謂“當位”公理;第五,凡當位之爻初四、二五、三上各相應者,是謂“相應”公理。[xvi] 牟先生對爻之位置所反映的六爻之相互關係非常敏感,以上概括是準確的。他的看法,前四條公理均爲靜態的存在,最後一條“相應公理”則爲爻的動用,如初、四爻相應,二、五爻相應,三、上爻相應。由六爻所代表的宇宙論言之,“相應”即是“感通”。漢易通過卦爻象數之路來觀陰陽氣化之變。
牟先生有關乾坤升降的討論,提出氣化交感互應的宇宙論,又研究了“據”(陽爻在陰爻之上)、“承”(陰爻在陽爻之下)、“乘”(陰爻居陽爻上者)的意義,互體問題和時空問題等,多有創發。[xvii]
牟先生對胡煦、焦循的研究非常深入,多有心得。熊十力先生對牟宗三有關胡煦生成哲學的闡發大爲讚賞。關於焦循的易學,牟先生指出,他是由卦爻象數的關係而建立了“旁通情也”的道德哲學。至於焦循《當位失道圖》的討論,“成兩既濟”與“當位元失道”的關係,能否稱爲“當位律”、“失道律”及其與“旁通律”的關係,焦循的混淆和牟先生歸納分析之不足,岑溢成先生的《焦循<當位失道圖>牟釋述補》一文論之甚詳。[xviii] 當然牟先生對焦氏旁通、相錯、時行等卦爻變動的基本原則的提揚,總體上是有很大意義的。
第二、晚年的易學觀 – 以 “窮神知化” 爲中心
牟先生對《中庸》《易傳》 的總體看法是,《易》《庸》是從天命、天道的下貫,從宇宙論的進路來講人性的,與孟子“仁義內在”,即心說性的道德的進路不一樣。
他指出 ,天命之性總是一種超越意義、價值意義的“性”。《易經•乾象》“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就是貞定這種性;《易•系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就是成的這種性。《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是盡的這種性。天、天命、天道下貫而爲性的“性”,不是材質主義的“氣命之性”。《易》《庸》之學是儒家從天道處說下來的人性論的傳統中的“客觀性原則”。[xix]
牟先生認爲,《彖》、《象》、《文言》與《系辭》,總名爲孔門《周易》方面之義理,代表了儒家精神。其中心思想在“窮神知化”(《系辭下傳》雲“窮神知化,德之聖也”)。《乾彖》《坤彖》集中體現此種精神,特別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貞”一語,頗值得深究。所謂“知化”者,知天地生化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即知“天道”。所謂“窮神”者,窮生化不測之神也,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神無方而易無體”等等[xx]。牟先生反復闡釋“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對以上《系辭》話語及相關思想的詮釋,牟先生強調的是:
(1)“窮神”即“知化”,反之亦然。“窮”不是科學求知,不是以器求之;“知”不是質測、知識之知。“窮神知化”是德性生命的證悟,是發之於德性生命之超越的形而上之洞見,其根據完全在“仁”。“顯諸仁,藏諸用”云云,即根據“仁”所證悟之天道也。天道並不是蹈空漂蕩的冥惑之事,同時要實現出來,有大用有實功。天道是“仁”亦是“誠”,天道的生化秩序(宇宙秩序)也即是一道德秩序,這是發之於德性生命的必然的證悟。[xxi]
(2)《易傳》是根據仁體的遍在而言天道即仁道,易道即仁道即生道。天道是“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生化不測之真幾、實體。《易》《庸》根據孔子的證境而顯揚,是內在性的證悟。德行生命的健行,而且又虔誠敬畏地“奉天時”,此即爲超越與內在的圓一。[xxii]
(3)《易經》之學即是由蓍卦之布算而見到生命之真幾。“極深研幾”云云,正是《易》之本義。這就是要透過物質世界上達至精無礙的超越實體。《易》學正是以生化不測之神或易簡之理來體證超越實體的。無論是天道的生化或是聖心的神明,都可以“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來形容之。這就是“寂感真幾”。所以,超越實體者即是此“寂感真幾”,神化與易簡是其本質之屬性。這都是由精誠的德性生命、精神生命的升進之所澈悟者。所證悟的是人生宇宙的本源。所以乾卦象傳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正是儒者超越智慧之不同於佛、老之處。[xxiii]
牟宗三不拘泥于現實功利和具體物象,著力發掘《易》學之中內蘊的理想價值、精神生命,肯定體證本體正是潔淨精微的“易教”的本色,促進人們養育心性,達到道德的高明之境。他對《易傳》的詮釋,與他“內在 – 超越”的哲學系統是一致的。在他看來,這種境界形上學,這種精神生命力的方向有其普遍性、永恒性與真理性,並永遠是具體的普遍。
五、唐君毅:天人內外相生相涵的圓教
唐君毅先生有關易學的探討亦是哲學性的,與牟先生有很多相近之處。他們二人相互影響,唐的很多探討較之以上所述牟晚年的探討,在時間上要早一些。
唐先生在《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貳》及《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中多處論及《易傳》。從這些標題:“《易傳》之即易道以觀天之神道”,“《易傳》之即繼言善、即成言性與本德性以有神明之知”、“運神明以知乾坤之道與即道言性”等等,不難看出唐的詮釋路向。
唐先生指出,關於“寂靜不動”之境而又“感而遂通”,從這一觀點看一切天地萬物,即見一切天地萬物皆由寂而感,由無形而有形,由形而上而形而下,即見一切形而下之有爲而可思者,皆如自一無思無爲之世界中流出而生而成。知此,即可以入于《易傳》之形上學之門。知一切物的生成皆由無形的形而上而有形而形而下,更觀一切物生成的“相續”,即見此萬物的生成,乃一由幽而明,由明而幽,亦由闔而辟,由辟而闔之歷程。《易傳》正是由此以言物之闔辟相繼、往來不窮,由象而形而器,以成其生生不已。這些器可以爲人所制而利用之,其利用之事亦有出有入而變化無窮,至神不測。[xxiv]
唐先生肯定人有超越於一定時空限制的“神明之知”,即無定限的心知。他說,物之感應變化之道即是易道,而神即在其中,故易道即神道。易無體神無方,不是易道之外別有神道。他發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進而討論神明之知與德行的關係。
他說:“人若無自私之心,亦不自私其心爲我所獨有,將此心亦還諸天地,而觀凡此天地之所在,即吾之心知、吾之神明之所運所在,天地皆此心知神明中之天地﹔則天地之現於前者無窮,此心知神明亦與之無窮。”[xxv]
唐先生解釋“神妙萬物”,特別指出這不是說“神超萬物”,也不是說“神遍在於萬物”。爲什麽呢?因爲說“神超萬物”,以安排計劃生萬物,則皆有定限而可測者也;說“神遍在萬物”,乃就萬物之已成者而言其遍在。這與言“神妙萬物”,即就神之運于方生者之不可測是不同的。唐先生在這裏把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與一元外在超越的基督教,與泛神論,區別開來。[xxvi]
唐先生認定,人們在觀照自然界之相互感應時,一面見自然物之德之凝聚,一面求自有其德行,與之相應;自然界啓示人當有德行,自然不是純粹的自然,而是有德行意義的自然。(這與方東美的看法十分接近。)中國學者善於隨處由自然得其啓示于人之德行上的意義。這與《周易•大象傳》等易教的影響有關。不僅人之德與天地之德相結合,而且如《周易•賁》之彖辭所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相對應。
就序卦之文而論,唐先生指出,《周易》之辨證法與西方之辨證法不同。《周易》多蘊含順承式的發展,西方辯證法多以正反直相轉變爲第一義。他重視乾陽而坤順以相承之義。另一方面,他認爲《周易》中所說的正反之相轉以見正反之相成,與西方辯證法的事物有內在的矛盾說不同。唐先生之本意,在強調中國哲學的和諧方式的辯證法與西方哲學的鬥爭方式的辯證法是不同的。
唐先生亦肯定《大戴禮記》的《本命》所說“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樂記》的“性命不同”與《易傳》的“各正性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順性命之理”與《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的重要。這一點亦同于馬一浮、牟宗三。
唐先生認爲:“人在其盡性之事中,即見有一道德生活上之自命。此自命,若自一超越于現實之人生已有之一切事之源泉流出,故謂之源於天命。實則此天命,即見於人之道德生活之自命之中,亦即見於人之自盡其性而求自誠自成之中,故曰天命之謂性也。至《中庸》之連天命以論性之思想之特色,亦即在視此性爲一人之自求其德行之純一不巳,而必自成其德之性,是即一必歸於‘成’之性,亦必歸於‘正’之性,而通于《易傳》之旨。此性,亦即徹始徹終,以底于成與正,而藏自命於內之性命。故人之盡性,即能完成天之所命,以至於命也。是又見《易傳》之言‘成之者性’,言‘各正性命’,‘盡性至命’,正爲與《中庸》爲相類之思想型態也。”[xxvii]此言《易》《庸》之同。
唐先生指出,《易傳》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及乾坤之鼓萬物之盛德大業等,其思想似純爲以一形上學爲先,以由天道而人性之系統。這與《孟子》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等直下在心性上取證者不同,也與《中庸》由聖人之至誠無息,方見其德其道之同於化育萬物之天德天道者,亦似有異。唐先生進而指出,《易傳》的陰陽、乾坤並舉,尤與《中庸》之舉一誠爲一貫天人之道者不同。此言《易》《庸》之異。
唐先生認爲,理解《易傳》先道後善而後性的入路是:須先在吾人之道德生活之歷程上及吾人如何本此心之神明以觀客觀宇宙之變化上,有所取證。這即是道德生活之求自誠而自成,即求其純一無間而相續不已,這就是善善相繼的歷程。這裏是先有繼之善,而後見其性之成,故先言繼善,而後言成性;非必謂繼中只有善而無性,性中只有成而無善,善與性分有先後之謂也。[xxviii]
唐先生指出,吾人之神明能兼藏往與知來,通觀往者與來者,即見往者來者皆運於有形無形之間,而由無形以之有形,又由有形以之無形,遂可見一切形象實乃行於一無形象之道上,或形而上之道上,以一屈而一伸。這個無形之道不是虛理,而是能使形“生而顯,成而隱”的有實作用的乾坤之道。
總而言之,唐先生說,乾坤之道與吾人性命的關係有兩種論法,《易傳》中均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第一種論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第二種論法。第一種論法是由主體到客體,第二種論法則相反。第一種論法是說,吾人之所以見宇宙有此乾坤之道,依吾人心之神明之知。人能有神明之知,乃出於吾人之心之性和吾人之性命。那麽,客觀宇宙的乾坤之道,是宇宙對吾人之性命之所呈,而內在於吾人之性命者。人之窮彼客觀宇宙之理,亦即所以自盡性而自至命。
第二種論法是把吾人之性命客觀化爲與萬物的性命同存在於客觀宇宙中的性命,亦同爲依於乾坤之道之所生之變化以自得自生而自成,以正其自己之一性命者。吾人的性命亦由乾道的變化而後得自生自成而自正者也。
這兩種論法互爲根據,互爲其本。由人以知天與由天以知人,可同歸於天人合德之旨,以見外窮宇宙之理與內盡自己之性,皆可以正性命而盡性至命。唐先生的結論是:“《易傳》之論性命與乾坤之道,在根底上,仍爲一視天人內外之關係爲相生而相涵之圓教,而與《中庸》同爲一具大智慧之書也。”[xxix]
以上我們知道,以《孟子》爲參照,牟先生認爲《易》《庸》是宇宙論的進路,重心是從天道下貫人性的客觀性原理。然而,同樣以《孟子》爲參照,唐先生不僅指出了《易》《庸》之同,又指出了《易》《庸》之異,雖同樣認爲《易傳》是由天道而人性的系統,但指出其包括了由主體到客體和由客體到主體兩方面的原理,此即乾坤並建。牟先生發揮《易傳》“窮神之化”的意義,認定是以“仁”爲根據的德性生命的證悟。唐先生論“神明之知”,則指出其包含有形與無形、形下與形上兩面,即道德實踐歷程、本心神明與客觀宇宙變化的相續不已。
六、現代新儒家的易學觀的意義
馮友蘭、徐複觀、張君勱等先生也討論過《周易》,特別是《易傳》,也發揮過《易傳》之旨。本文之所以略而不論,是因爲他們大體上未曾把對《易傳》的詮釋與自家的哲學體系或哲學性思考相融,或僅是以思想史家、哲學史家的立場加以闡發的。
前面我討論的熊十力、馬一浮、方東美、牟宗三、唐君毅五家的周易思想,相互發明者在在皆是。除牟先生早年外,他們均未(包括牟氏中晚年)理會象數學,均未從學術性路數具體而微地研究易學與易學史。五先生的共同之處是,抓住《易傳》的一些關鍵性、哲理性話語予以創造性解讀,在現當代重建了《易》的形上學,特別是道德形上學,並從形上易體的存有與活動的兩面及其統合上加以發展。
五先生所論容或有一些差異,然通而觀之,不難發現他們雖出之于宋易又推陳出新,賦予《周易》以現代哲學的意蘊。其價值與意義是:
- 不再拘束於繁瑣的形式系統,亦不拘泥於物化的世界,提揚《周易》所代表的儒家乃至中國哲學的精神方向、價值世界,激勵中國人的真善美相融通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並形成信念信仰,以安身立命。
- 發揮《易傳》的創造精神,撐開“用”、“現象界”、“形下界”和“外王學”,面對西方世界的挑戰,面對現代生活而開物成務,崇德廣業。此即體用不二、乾坤並建的題中應有之意。
- 以現代哲學的觀念與問題意識重點闡發了《周易》哲學的宇宙論、本體論、生命論、人性論、境界論、價值論及其間的聯繫,肯定了中國哲學之不同於西方哲學的特性是生機的自然觀,整體和諧觀,自然宇宙和事實世界涵有價值的觀念,至美至善的追求,生命的學問和內在性的體驗。
- 重建了本體論和宇宙論,證成了超越性與內在性的貫通及天與人合德的意義。重釋“窮理盡性至命”、“繼善成性”等命題的價值,肯定人有“神明之知”,能“窮神知化”,從而成就了儒家式的道德形上學。
中國哲學:對話與建構
楊國榮
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的哲學界往往把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分爲哲學領域當中的主要分支。無論從空間的角度看,還是從時間維度看,這都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現象。從空間上看,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其他地區,一般很少對哲學做這樣一種劃分,就西方的哲學界而言,除哲學史外,哲學的分支一般被區分爲倫理學、政治哲學、科學哲學、邏輯學、語言哲學、心智哲學,等等;從時間上說,儘管西方哲學在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哲學在20世紀初已傳入中國,但20世紀下半葉以前,中、西、馬在哲學領域並未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從邏輯上看,這種區分無疑存在種種問題,事實上人們對上述劃分以及由此形成的格局也已提出種種責難和批評(這種批評以後可能還將延續),然而,不管人們如何評價,有一點是無可否認的,那就是自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在中國的哲學界,以上區分已經成了一種本體論的事實。
從哲學的研究和發展來看,對這種既成的哲學形態,我們究竟應當如何來看待?它對中國哲學的發展是不是僅僅只有負面的意義?我想,在責難與質疑的同時,也許還可以從一個比較積極的、建設性的角度來思考、評價這種現象。作爲重建或發展當代中國哲學的現實背景,上述區分在某種意義上也爲我們今天的哲學思提供了多重的理論資源。
如所周知,西方的主流哲學一般不把中國哲學看作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它們也較少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創意義,可以說,中國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維成果,基本上在西方主流哲學的視野之外。這種觀念,無疑也限制了西方哲學本身的發展:將中國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排除在真正的哲學領域之外,使之只能限於西方哲學這一單一的傳統和資源之中,而不能將其視野擴展到其他具有豐富內涵的哲學系統。事實上,忽視多元的哲學智慧,似乎也導致了西方主流哲學的貧乏化、狹隘化。按其本來形態,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都包含著具有原創意義的思維成果[4],把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都作爲當代哲學建構的資源,這對於進一步的哲學思考來說,無疑將提供更寬廣的背景。目前所提出的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對話,也應當從上述角度去加以理解。
就對話本身而言,問題常常會涉及到其內在的、實質的意義。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相互對話,顯然不能只限於從事中國哲學、西方哲學或者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者各自表述自身的學科立場和觀念,使彼此之間能相互比較、相互理解,如果僅僅停留在這樣的層面,則似乎依然囿於某種學科之域。從更內在的層面看,哲學對話的真正意義涉及哲學究竟是什麽,或者說哲學的真實形態應當是什麽的問題。哲學究竟是什麽或何爲哲學本身是一種本原性的追問,現在之所以要以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話這樣一種方式來思考這一問題,其緣由在於這三者之間的劃界、區分,已經使人們習慣於從一個相對狹隘的學科立場出發去理解哲學,後者往往對哲學本身的理解帶來種種的限制,從而難以達到哲學的真實形態。與何爲哲學的真實形態相聯繫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達到或回歸哲學的真實形態,用康得式的方式來表述,也就是:真實的哲學形態如何可能?
哲學(philosophy)的原始意義涉及智慧,從某種意義上說,哲學就是一種智慧之思,是對智慧之境的一種綿綿不斷的追求。作爲智慧之思,哲學以性與天道爲物件,並指向統一的、具體的存在。與智慧相對的是知識,後者主要限於對存在的某一個方面或者某一個層面的把握。在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彼此劃界的背景之下,人們往往習慣於僅僅從某一種角度、某一個層面去理解存在,由此把握的往往並不是具體的、統一的存在,而只是特定視域中的物件,後者所體現的,事實上是一種指向知識的追問。不難看到,從一種分離的、劃界的立場出發去理解哲學,往往意味著將作爲智慧之思的哲學降低爲作爲知識形態的哲學。這種狀況的形成,從理論上看,和哲學本身的職業化、專業化,以及哲學家的專家化趨向,無疑有相當的關係。如前所述,哲學本質上是智慧之思,從事哲學思考的哲學家,首先是志於道的思想者。然而,一旦哲學成爲某種職業或專業,那麽哲學家也就從智慧的追求者,轉化成一個僅僅從事某一層面、某一個方面思考的專家。職業化、專業化的工作涉及的主要是存在的特定領域、特定方面,專家的關注之點,也相應地限於某一領域或方面,哲學的職業化與專業化以及哲學家的專家化,在歷史與邏輯雙重意義上導致了哲學的知識化。以此爲背景,所謂回到哲學的真實形態,也就是超越對哲學的知識化理解而達到哲學作爲智慧之思的本真形態。可以說,正是這種回歸,構成了哲學對話的內在意義。
對哲學真實形態的回歸,涉及多重方面,具體而言,我們需要討論和關注的至少包括如下問題。
首先是史和思,或者說哲學史和哲學的統一。我一再強調,在哲學領域裏,史和思、哲學和哲學史無法截然分離。從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各自形態及相互關係看,我們習慣上往往把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理解爲哲學史,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爲哲學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通常也被簡稱爲“原理”)。這種理解是很成問題的。事實上,不管是在中國哲學的歷史上,還是在西方哲學的歷史上,現在被我們作爲哲學史物件來考察、研究的體系,在其形成之際,更多地呈現爲理論思考的結晶,換言之,它們在成爲哲學的歷史之前,首先是哲學的理論;哲學的理論和哲學的歷史,在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中,都並非截然分離。同樣,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既是一種哲學的理論,同時又是人類文化長期發展的成果,有其歷史的前提、歷史的背景,而並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理論的形態。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說,不管是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都既是一種已然(既成)的形態,又表現爲一種生成的過程,具有開放的性質。就中國哲學而言,當代中國哲學的思考便可以看作是廣義上的中國哲學的延續,同樣,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如此,它既通過學史上的革命變革而延續了哲學史,自身又展開爲一個發展過程。史和思,哲學史和哲學理論的如上聯繫,決定了我們既不能就史而論史,也不能離開史來從事哲學的思考。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話,同樣涉及哲學的歷史和哲學的理論之間的互動,而它所指向的,則是哲學的真實形態。
對話所涉及的另一個問題,是中西哲學之間的關係。中西哲學在歷史上曾經各自作爲一種相對獨立的發展系統,然而,在歷史已經超越地域的尺度而成爲一種世界的歷史、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爲當今世界基本趨向這樣一種條件下,僅僅拘泥於地域性的視野,顯然是不合理的。與世界歷史的觀念相應,我們也同樣需要一種世界哲學的觀念。在世界哲學的觀念之下,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都是世界哲學的一種財富,都應該被理解爲世界哲學中合法的家族成員,理解爲延續、發展世界哲學的一種共同的資源。這種世界哲學的視野是哲學回歸真實形態的基本要求。
從研究方法看,這裏涉及中西哲學比較的問題。中西哲學的比較的意義究竟何在?如果比較僅僅被理解爲羅列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各自特點,指出什麽是二者的相同之處,哪些是二者的差異之點,等等,那麽,這顯然是較爲表層的。從哲學對話的角度看,比較的真實意義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是歷史之維。在這一維度上,比較意味著爲深入地理解某一哲學系統提供一種理論的參照。以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如果能獲得西方哲學的視域,無疑有助於具體地揭示、澄明中國古典哲學的概念、命題、學說中的內在理論意蘊,真實地彰顯其豐富而深沈的內容,使之獲得能夠與其他哲學對話的形態,並真正融入世界哲學。同樣,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和理解,如果能以中國哲學作爲參照背景,也可以進一步去發現它的一些獨特意義。在單一的視域下,無論是中國哲學,抑或西方哲學,其內在的意蘊往往都難以充分地敞開和展示,而在不同的理論背景中,一種哲學系統的深刻意義就容易被揭示和把握。另一方面,從理論建構或發展當代哲學的層面來看,比較的意義在於爲今天的哲學思考提供理論的資源。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都積累了具有原創意義的思維成果,這些成果不僅僅是歷史中的存在,它同時也構成了當代哲學發展的源頭,具有建構功能,中西哲學對話更內在的意義,無疑應當從上述方面加以理解。
哲學的對話除了展開於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學科領域之外,還可以從一個更寬泛的層面去考察。從後一角度看,哲學對話往往表現爲不同的哲學系統、不同的哲學傳統,以及不同的哲學觀念、立場、進路之間的相互激蕩和互動。首先是形上和形下之間的關係。哲學總是離不開形上之思,所謂形上之思,我們可以寬泛地理解爲對存在的終極追問;形下之域,則主要涉及經驗世界和日常生活。哲學既離不開對存在的終極追問,也需要不斷地關注經驗世界和日常生活。一般說來,經驗論的傳統,往往比較關注經驗世界和日常生活,理性主義則常常關注於形而上之域。在這裏,形上和形下之間的關係,常常就展開爲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緊張。從哲學對話這一角度看,這裏事實上涉及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溝通和互動,而對話的意義則進一步體現爲揚棄不同哲學傳統的理論局限,達到更寬廣的理論視野。
廣而言之,哲學的對話也涉及哲學的思辨和知性觀念之間的關係問題。這裏所說的哲學思辨,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涵義。其一,與人的整個精神世界相聯繫的思與辨。金岳霖曾區分了元學立場和知識立場。在他看來,元學立場應當以整個的人作爲主體,借用他的表述,哲學思辨也可以理解爲以整個的人作爲主體而展開的哲學思考。具體而言,它並非僅僅限於邏輯的、理性的規定,而且也著眼於情意、體驗、直覺、領悟等方面,質言之,以人的具體性爲出發點。哲學思辨的另一個含義是辯證的思維。我一再指出,我們不僅要回到康得,而且我們也應當在某種意義上回到黑格爾,而與黑格爾相聯繫的思維成果之一,便是辯證思維。與哲學思辨相對,知性的立場或者知性的觀念主要也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知性的思維方式,後者的特點是將整體分離爲部分、把過程截斷爲一個個階段,它在總體上表現爲一種區分、劃界的立場。知性思維以人的抽象存在爲主體,關注的僅僅是存在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層面的規定。與知性思維相聯繫的另一個方面是邏輯的分析。對世界的把握,既要以人的整個存在、以人的整個精神世界作爲出發點,同時也需要一種辯證的觀點,以揚棄分離的、抽象的立場,達到具體的、統一的世界。同樣,哲學的思與辮離不開嚴密的邏輯分析和論證。哲學的概念、命題應該進行清晰地辨析,提出一個論點,必須經過嚴密的推論,等等。就近代哲學及現代哲學而言,康得與黑格爾,現象學和分析哲學便表現了不同的哲學進路,而哲學思辨和知性立場之間的溝通,事實上也涉及到不同哲學進路之間的相互對話和相互溝通。由此,我們可以賦予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話以更具體、更實質的內涵,或者說,對哲學對話作更廣意義上的理解。
從 重 新 評 價 到 互 動 對 話
——臺灣對大陸近二十多年儒學研究的述評
陳衛平
內容提要 臺灣學界在1980年代提出“文化中國”,意謂大陸和臺灣在文化傳統上存在著一致性。因此,臺灣學界對於大陸近二十多年的中國哲學研究比較關注。在1949年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臺灣以繼承和發揚儒學爲己任,而大陸發展到文革期間把儒學作爲徹底打倒的物件,因此臺灣對於大陸中國哲學研究的關注自然就集中在儒學方面。1949年以後,港臺形成並活躍著現代新儒家,而現代新儒家注重闡發孔孟和宋明理學,現代新儒家在1980年代以後又成爲大陸學術界研究的重要課題。於是,臺灣學術界最矚目於大陸儒學研究中有關孔孟、理學、新儒學的研究。同時,在一般層面的儒學研究上,由於港臺新儒家注重闡發儒學的宗教意蘊和現代意義,因而對大陸有關儒教說、中國馬克思主義與儒學傳統的爭論也有所評述。
一
大陸近二十多年對於儒學研究,是從對孔子的重新評價開始的。熊自健所著的《中共學界孔子研究新貌》甚爲全面地評述了大陸1978年至1988年的孔子研究,包括研究孔子的方法論以及孔子的道德哲學、宗教思想、美學、認識論、政治思想、教育學等方面。這裏擇其與哲學相關部分的評述。
熊自健注意到大陸對孔子的重新評價,首先是與研究方法的出新相聯繫的。他以李澤厚、匡亞明、張岱年的方法爲代表,指出李澤厚從文化心理結構來研析“仁”,指出仁學結構的四因素及其相互關聯;匡亞明強調不能機械套用“存在決定意識”來分析孔子的人本哲學思想體系,提出對孔子思想遺産實行三分法,即分爲封建性意識、有生命力的智慧、精華與糟粕相混雜三方面;張岱年注重對哲學範疇、命題的理論分析,由此來認識孔子的哲學體系及其特點、傳承;認爲這些方法“超出了簡單階級分析的模式,深化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探索孔子思想內在的統一性具有方法論的自覺,要求避免各執一端片面地理解孔子”;然而,牟宗三指出的宋明儒從道德實踐的工夫來體認孔子,要比上述的方法“更具有活潑動人的生命”。關於孔子道德哲學的研究,熊自健紹述了朱伯昆、魏英敏、馮友蘭、匡亞明、羅佐才、李啓謙、楊景凡、嚴北溟、楊伯峻、李澤厚、蕭箑父、任繼愈、徐長安等人的有關論著,在孔子論道德的意義與道德行爲的來源、孔子道德哲學的核心、孔子道德哲學的體系這些問題上的各種觀點,認爲“中國大陸學界近年來對孔子道德哲學的解析有濃厚的學術氣息,脫離膚淺的政治謾駡”,“最令人側目的是,大多數的學者主張對孔子的道德哲學吸收其精華,進行創造轉化,爲社會主義的道德生活于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哲學服務”;但是,“牟宗三先生所闡明孔子成德之教的精義,是大陸學界解析孔子道德哲學時尚未達到的境界”。關於孔子認識論的研究,熊自健分析了張岱年、任繼愈、鍾肇鵬、茅亭、楊鳳麟、馮契、劉邦富、王舉忠以及北大哲學系與蕭箑父等主編的兩本《中國哲學史》等論著,認爲這些論著涉及到了孔子關於知識的來源與性質、認知的方法與過程、知識與道德實踐的關係等問題,重新探索孔子的認識論,在“努力地辨析孔子認識論在中國哲學史的意義與作用上,頗見功力”,但往往糾纏於唯心、唯物的問題上,對於最能表現孔子認識論特點的知識與道德實踐的關係問題,較少有人提出討論,而牟宗三在《現象與物自身》“所開出儒學認識論的新方向,正好反照出中國大陸學界探索孔子認識論的各種限制”。 對孔子美學的研究,熊自健以劉綱紀、張懷謹、葉朗、鍾肇鵬四人的研究成果爲代表,認爲劉綱紀以結構分析的方式來探討孔子的美學,孔子從仁學出發,以個體與社會的統一去觀察美和藝術的現象,強調審美和藝術是陶冶人的思想情感的重要手段,分析了藝術的社會作用,又提出了美的本質是與道德上的善相統一,把“中庸”作爲美學批評的尺度;張懷謹從孔子的詩樂理論來探討孔子的美學,由此把孔子的美學思想概括爲由詩樂而達到理,又由禮而歸乎仁,指出孔子審詩正樂的美學理想與天下歸仁的理想是結合在一起的;葉朗以孔子的審美觀念爲中心,從其提出的美學範疇和命題來論述孔子的美學思想,強調探討審美和藝術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是孔子美學的出發點和中心,並說明了孔子“興觀群怨”、“大”“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所具有的審美意義;鍾肇鵬把孔子有關美和文藝的言論彙集在一起,分類論述,以文質彬彬爲孔子美學思想的綱領,由此詮釋孔子的美善統一、詩教與樂教、語言修辭等思想。他認爲從上述四人的研究成果可看到:“研究方法受到歷史唯物主義的限制最少”,“不落在‘基礎、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架構中來解析孔子的美學,而從孔子美學本身的性質與內涵進行研析”;比較一致地注意到了孔子美學與其仁學的關聯,“因此他們探討孔子美學是具有整體性的脈絡”;辨析了孔子美學的價值層次,不是“把孔子有關美和文藝的論點放在同一平面上來處理”,而是注意到它們在孔子美學思想中有不同的層次;一致認爲美善統一的理想是孔子美學的最大特徵,並指出伴隨這一特徵而來的一些局限性;有待努力的是加深對孔子仁學的體察,由此才能進一步詮釋出孔子美學的精彩之處,在這方面馬一浮的《論語大義》和臺灣大學教授張亨的《論語論詩》可作參考。[xxx]
大陸的美學研究,包括對中國傳統美學的研究,馬克思的《巴黎手稿》是重要的理論依據。陳懷恩在肯定李澤厚、劉綱紀的《中國美學史》“堪稱爲近代處理中國美學的皇皇巨制”的同時,對其用《巴黎手稿》來詮釋孔子的仁學和審美態度的可行性提出質疑。他認爲該書把仁學詮釋爲以社會性的感情爲本,而馬克思講的社會感情是一種歷史的抽象,孔子的道德情感則是實存的,兩者“在出發點上就有差異”;馬克思和孔子雖都認爲審美活動是自由境界,但就孔子來說,“一般人的藝術享受和藝術創作都可以暫時地達到自由、審美的境界”,就馬克思來說,純美的自由境界要等待人類的“人性的感官”、“社會感官”完全創造出來才能達成,而這又與完全廢除私有制相聯繫,因此,“就實踐過程來看,兩者卻是涇渭分明的”;該書以“藝術作用即社會性感情的交換功能”來詮釋孔子的興、觀、群、怨是否有公式化的問題;他還指出該書既認爲孔子以善爲美的內容,又說孔子承認形式美有獨立意義,這是互相矛盾的。[xxxi]
在大陸研究孟子的論著中,李明輝對楊澤波的《孟子性善論研究》給予高度的評價。他說此書“是中國大陸第一部突破馬列教條、從自己的觀點來討論孟子性善論的專著。1994年筆者爲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辦‘孟子學國際研討會’時,曾廣泛瀏覽中國大陸有關孟子學的著作,發現千篇一律都將孟子的性善論說成唯心論,完全無法進入其思想脈絡之中。因此,儘管楊澤波此書仍有若干值得商榷之處,但已令人耳目一新”。[xxxii]但對其耳目一新之處和值得商榷之處都未有進一步的論述。
楊祖漢則在充分肯定楊澤波的著作是“近年來孟子學的相當有水準及富個人見解的著作”的同時,對此書中有關牟宗三的孟子研究的一些評議提出了商榷意見。首先,關於孟子與康得。牟宗三認爲康得和孟子都是道德自律形態的,楊澤波則認爲不然,因爲康得重理性輕情感,並把道德情感納入他律之中,而孟子尊重包含豐富情感性的良心本心,很難戴上道德自律的桂冠。楊祖漢維護牟宗三得觀點,論證孟子的學說“是自律的倫理學,不特如此,康得的意志底自律說,必須承認孟子的理論,才能證成”。其次,對道德形上學的理解。牟宗三沿著孔孟“踐仁以知天”、“盡心知性知天”之義,闡發“道德形上學”,楊澤波認爲,這樣的道德形上學是爲了使本心善性有穩固的基礎,從而走向把心體性體不僅作爲道德根源而且作爲宇宙真實根源的泛道德主義。在楊祖漢看來,這是對牟宗三的誤解,因爲牟宗三從孔孟出發,區分了道德的形上學與形上學的道德學,後者是爲心性找形上學根據,而這正是牟宗三所反對的。再次,圓善問題。所謂圓善,即德福一致,牟宗三認爲儒、道、釋對於圓善如何能實現的問題,較之康得有更圓滿的解答,楊澤波認爲儒家幸福觀也許比康得圓滿,但其並沒有解決康得所沒有解決的問題,即在實際上保證有德之人一定能享受到現實的幸福。楊祖漢指出,這是把幸福理解爲滿足感性欲望而導致的,現實的幸福是人的存在情況使他感到稱心如意,是一種狀態的理念,因而儒家的聖人一切隨心而轉的境界就是現實的幸福。第四,牟宗三以孟子爲標準,分宋明儒學爲三系,以朱熹爲“別子”, 楊澤波批評這一標準有偏頗,因爲孟子和荀子各繼承了孔子的內求或外求之一翼,所以不可以孟子爲孔子嫡系真傳。楊祖漢申論牟宗三對孔、孟、荀的分別,以爲孔子雖然講外學,但重點在反己自省的德性之學,故孟子所偏者小而荀子所失者大,承繼孔子方向的自然是孟子,以此來看朱熹用講知識的方法來講道德,與孔孟不相應,認其爲“別子”也是合理的。總之,楊祖漢認爲在楊澤波的孟子研究中,對牟宗三的孟子研究的理解不太恰當,並認爲這往往是大陸學者的通病。[xxxiii]
二
對於大陸宋明理學的研究,傅偉勳和曾春海都注意到了侯外廬等主編的《松明理學史》。傅偉勳的評論較爲具體,提出該著作有兩個特色:強調了長期不被重視的元代理學;注意到理學發展與當時社會發展的關係。但對該著作的序言提出科學的理學史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則不以爲然,認爲這是混淆了科學形態、哲學形態、意識形態這三種馬克思主義的區別。[xxxiv]作爲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劃”成果之一的論文集《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中國大陸與臺灣篇》,收有香港學者鄭宗義《大陸學者的宋明理學研究》一文,對大陸的宋明理學研究有甚爲詳細的分析。他認爲大陸的宋明理學研究,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949年至八十年代初,研究幾乎完全套用唯心唯物的二分法、階級出身等教條主義,對理學大抵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第二階段自八十年代處至八十年代末,此時已不滿教條的生搬硬套,而提倡通過重要範疇的分疏來掌握理學,對理學有正、負兩方面的評價,但仍未脫教條陰影;第三階段自八十年代末至2000年,研究開始完全擺脫教條的色彩,強調文獻的解讀與爬梳,且多有參考借取海外學界的觀點說法,以爲進一步思考析論之所資,但對理學的瞭解還不免重心性而輕天道,而有一偏之虞。他對第一階段的評估,這裏只敍述與本文有關的部分。他認爲侯外廬等主編的《宋明理學史》在研究方法以至內容結論上均有大不同於貫穿唯心唯物二分法的《中國思想通史》,反映了大陸學者的理學研究在八十年代中期已轉入另一階段,書中很多篇章實際上是通過分析厘清宋明儒的各個範疇、命題及問題來立論的,特別是對材料所下的考證工夫,例如仔細指出宋明儒那些觀念受到佛、老的影響,則深具參考價值。對於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宋明理學研究,他的看法是“馮先生雖自詡從比較哲學的觀點揭示宋明理學的中心課題乃關乎什麽是人與怎樣做人的‘人學’”,但視野常常轉到共相與殊相的問題上,與《中國哲學史》的舊說大同小異,“未能會心于宋明儒天道性命相貫通的睿識”。他對第二階段的評估,以張立文的著作爲代表,認爲張立文肯定理學是體現當時時代精神的思潮,但由於強調回到它那個時代中去考察它,因而很難重釋出理學的現代意義;張立文以範疇分析方法透視宋明理學,“從方法論的角度看,絕對值得肯定”,但其對理學範疇的分析,依然是唯心、唯物那一套,而且以世界本原問題作爲研究理學的視野,無法瞭解理學貫通天道性命的特質;在這一階段,張岱年的《宋明理學評價問題》和《宋明理學的心性概念的分析》,“竟一反其唯物論立場,運用道德自覺性與西方哲學理性主義的觀念來闡釋宋明儒的心性之學,雖只簡略點及而未見仔細的鋪陳,惟已隱約透露出大陸學者的理學研究在九十年代又將邁進另一新階段的消息。而這消息後來則具體表現在張先生的弟子陳來先生的著作中”。他對第三階段的評估,以陳來的《宋明理學》爲代表,認爲陳來“更能儘量讓文獻本身說話,並且在義理上幾完全棄用唯心、唯物等教條用語”,其借用西方哲學中的實踐理性與普遍性道德法則等概念來辨解理學之理的實義,反對將理簡單化地看成社會規範或禮教,“可知他對理學中的心性部分確有相當的契會”;不過,其對理學的理解有重心性輕天道的片面。最後,他的結論是“大陸學者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研究,迄今似仍未能完全契接宋明儒天道性命貫通的微意”,因而需要與牟宗三的理學研究有進一步的對話交流、視域交融。[xxxv]
傳統儒學自漢以後成了經學,因而對儒學的研究不能不涉及經學。同時由於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有研究經學的計劃,所以在關注大陸的理學研究的同時,也對大陸的宋代經學研究有所關注。許維萍著文詳盡地介紹和評價了大陸文革後研究宋代經學的概況。該文指出:有關宋代經學的研究,“中國大陸在許多領域、許多課題上,都有不俗的表現,值得臺灣學者借鏡”;大陸研究《周易》的成果,在各經中數量最多,主要是從哲學和史學的角度進行研究,這與臺灣以中文系、所爲主研究《周易》很不相同。宋代凡有《易》說傳世的大家,都有專文研究,其中以研究朱熹《易》學的爲最多,“朱熹可以說是最受大陸學者矚目的宋代《易》學家”,也有針對《易》說中某一問題深入探究者,如金祖孟的《論邵雍的“天圓地方”》就是典型的例子;《詩經》學的研究,是以朱熹《詩集傳》爲中心的,其他宋人的《詩經》學著作,研究者比較少,成果也比較有限,對於朱熹《詩集傳》的研究論文,有概論性質的、有分析《詩集傳》纂例的、也有與《毛詩序》進行比較研究的、還有從聲韻和訓詁入手的;對於宋代《尚書》學的研究議題比較零散,論文數量只有十餘篇,這些論文有概論性的、有研究某個經學家《尚書》學的,值得注意的是若干從版本目錄學角度切入的論文;在《春秋》學方面,沒有專門研究宋代《公羊》學或《谷梁》學的論文,只有關於宋代《春秋》學的概論性論文和研究呂祖謙《左傳》學的論文,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領域的版本研究,如王清原的《遼寧新發現宋德佑刻本春秋集注》;對於《四書》學的研究,“不論在數量上或是研究題目的寬廣度上,中國大陸的研究成果都是相當有限的”,在這些成果中,有的屬於“《四書》研究史”的範疇,有的從宋代學者的《四書》學角度出發,有的屬於古籍整理的點校;大陸的《禮》學研究有待開發,在有限的成果中,姚瀛艇的《宋儒對〈周禮〉的研究與爭議》是唯一研究《周禮》的文章,文中肯定歐陽修的疑經精神,這與臺灣晚近研究經學史的學者的態度相一致,但該文從李覯出身于中小地主階層和階級矛盾等分析其提出《周禮致太平論》,則很典型地反映出大陸學者對經學問題的切入方式;宋代《爾雅》學的研究,大陸只有一、二人參與,除石雲孫點校的《爾雅翼》之外,所有的論文由馮蒸一個人包辦了,並且全部集中在研究《爾雅音圖音注》一書上,由此“可以看出這個領域仍然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關於石經的研究論文約有五篇,議題零星,篇幅也不長,有系統、較深入的研究成果有待進一步的努力。[xxxvi]
在儒學發展史上,取代宋明理學而興起的是清代乾嘉經學。因而宋明理學的研究和乾嘉經學的研究有著緊密的關聯,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實際上是將這兩方面的研究相配合的。於是,臺灣學者對大陸的乾嘉經學的研究也頗爲關注。蔣秋華撰有專文對大陸學者的乾嘉揚州學派研究予以考察。他指出在1980年以前,大陸學者對揚州學派的研究,只有不到20篇的相關論著,而且重心多半放在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訓詁學著作上;張舜徽是比較全面研究揚州學派的第一人,“他的研究,影響深遠,不僅開啓了近代學者研究揚州學術的風氣,他的許多論點也爲後來研究者所襲用”;1980年代以來,比較集中的研究,以揚州師範學院爲重心,祁龍威教授主導著研究的推進;在研究成果中,關於小學的成果占了大部分,有意識的專論是少數,且創立新解的並不多。[xxxvii]
三
在對傳統儒學重新評價的同時,實際上已經蘊含著與儒學的對話,當然,這種對話更集中地表現在大陸研究對港臺新儒學的興起。杜維明、劉述先較早把新儒學向大陸作了介紹,並首先提出了當代新儒學、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互動對話。爾後對新儒學在大陸廣泛流傳起了很大作用的方克立也倡導這三者的互動對話。大陸哲學界與新儒學的互動對話促進了雙方的新儒學研究。大陸方面認識到與新儒學對話,就必須研究新儒學。於是,1986年由方克立和李錦全負責的“當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被列入國家重點研究課題,大陸的新儒學研究從此有效地展開,並在相當的時期裏成爲學術界聚焦點之一。同時,大陸的新儒學研究也促進了臺灣的新儒學研究。李明輝指出,臺灣中央研究院確定“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劃”的“直接背景,則是中國大陸的學術轉向”,即開始正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與意義,把“當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列入“七五”期間國家重點研究課題之一,由方克立和李錦全負責,“由於大陸學術界的人力充沛,一經動員,很容易形成局部優勢,這對臺灣的學術界自然造成很大的挑戰”。[xxxviii]作爲回應這一挑戰的當代儒學研究計劃一直持續至今。
在大陸與新儒學的互動對話中,這一領域的意識形態對立逐漸疏緩。李明輝在1991年評價方克立主持的課題組的研究成果時,以爲鄭家棟的《現代新儒學概論》“標示了大陸新儒學研究的第一階段之高峰”,態度客觀,少有刻意的曲解,“作者也有不錯的理解力,避免了一些流行的誤解,有時甚至能澄清若干誤解”,例如對當代新儒家與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作了分疏,其缺點是對台港和海外新儒家的研究較弱,表現了與他們的隔膜,因而對他們的“良知坎陷”、“內聖外王”理解有誤;然而,由於方克立並非將新儒學研究單純地看作一般的學術研究,而是看成意識形態鬥爭的一部分,因而在該課題組的論文集《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第一集的多數論文中,“到處都可以見到作者套用馬列主義觀點提出批判”,於是在他看來,“中國大陸新儒學研究的最大阻礙在於意識形態的限制,這項限制形成其研究成果無法突破的瓶頸”。[xxxix]對於這樣的評價,方克立提出了反批評,李明輝又對此作了回應。[xl]這些往返論辯可以說既有學術上的分歧更有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或者說這些學術上的分歧是與意識形態的對立相聯繫的。到了1996年,李明輝在看到大陸的鄧小軍和楊澤波的著作後,認爲他1991年所作的“今天在中國大陸研究當代新儒家的學者,不論其個人對新儒家的評價如何,多半不能擺脫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之影響”這項論斷,“可能有修改之必要”。[xli]在四年之後的2000年,他說“時至今日,大陸的學術界已有了不小的變化,非意識形態化的趨勢日益明顯”。[xlii]這是否意味著在他看來往日制約大陸新儒學研究的瓶頸正在消解?其實,意識形態對立的和緩是雙向的,正如林安悟所說,在大陸與新儒學的對話互動中,“當代新儒學原先的反共根芽倒是自然而然的被淡去,這一方面可能是有意的忽略,另一方面則顯示大陸已不再是意識形態挂帥”。[xliii]
大陸與新儒學對話的重要方面,是儒學與現代化的關係或者說儒學是否具有現代意義。因爲大陸長期以來認同“五四”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以爲儒學是現代化的阻礙,而新儒家把儒學作爲發展當代中國現代化的思想資源,強力闡發儒學的現代意蘊。在1980年代的前期,雖然大陸還未展開對現代新儒學的認真研究,但對於新儒學的“返本開新”(返傳統儒學之本而開科學民主之新)已有所討論。王章陵從朱日耀、薛湧、毛丹、包遵信、耿雲志、黃萬盛等人的論文中,注意到當時大陸對這種“返本開新”論持有贊同和否定兩種態度,而否定態度是占上風的。他對否定“返本開新”的觀點提出了批評:大陸學界以爲儒學與專制制度相適應,因而不能疏導出民主,,其實,“中國傳統政治雖非西方民主,但並非專制,這種非專制的傳統共和政治,實即奠基於儒學的人文主義思想”;大陸學界把儒學看作是輕視科學知識得到的理想型學說,其實,如錢穆、胡適所論證的,儒學重並不缺乏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因此“說儒學裏根本不能産生科學,那都是偏見”;大陸學界認爲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不是以儒學爲動力,只是西方模式的移植,實際上儒學是“四小龍”經濟起飛的文化因素,即以儒家倫理調節人際關係,建立和諧社會,形成“經濟發展之必要前提”。[xliv] 劉述先認爲,包遵信反對新儒家關於儒家傳統與現代化並不相悖的觀點,把儒學看作現代化的負面包袱,是因爲他把大陸現存的一些“封建”的東西歸咎於儒家,把西方的現代化看作是現代化的唯一模式。包遵信認爲新儒家試圖用傳統儒家的智慧解決後現代的一些偏失是徒勞的,因爲這些偏失的出現是必然的,同時也沒有經驗能證實新儒家這種努力的有效性。對此劉述先指出,新儒家並不認爲後現代的偏失是必然的就可以聽之任之,而是要有批判意識,新儒家力圖建立人的“終極關懷”,不能因爲其在現實上缺乏急效就斷定爲無用。[xlv]如果說王章陵和劉述先是批評了大陸不贊同返本開新說的觀點,那麽高柏園則注意到了大陸學者蔣慶完善新儒學開出新外王的努力。蔣慶著文指出,新儒學在外王問題上有兩個缺失:一是從心性儒學開出外王,忽視了政治儒學的資源;二是以科學民主爲新外王的標準,有變相西化之嫌;由此試圖從政治儒學來開出新儒學的新外王。高柏園認爲,蔣慶爲新儒學的外王思想提供新資源的用心十分可敬,對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的區分對新儒學也有正面的作用,但其努力並不成功,因爲其論證“在在充滿缺失”,“缺乏有力的支援”,“對儒家及新儒家的理解也不乏許多可商榷之處”。[xlvi]李明輝頗感興趣的是大陸出現的與返本開新說相近似的著作,如鄧小軍的《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邏輯結合》,認爲此書“是要證明儒家思想雖不等於現代民主思想,但兩者之間具有邏輯關聯。熟悉當代新儒學的人對於這種看法一定不會感到陌生。但是它出自一位中年大陸學者之手,而且書中完全見不到馬列術語,這便透露出一項值得玩味的訊息”。[xlvii]這種值得玩味的訊息,就是經過與新儒學的對話,認爲儒學仍有現代價值,應當成爲當代中國哲學的思想資源的觀點,已在大陸佔據主導的地位。林安悟指明了這一點:“兩岸自八十年代以來,多有互動、影響。明顯地,港臺新儒學的影響最大”,大陸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裏,傳統文化逐漸爲人重視,當代新儒學在這樣的波動下,進到中國大陸,成了一重要的穩健力量,做爲改革發展過程中的調節力量之一。此時,傳統儒道佛思想的和諧性原理取代了原先的鬥爭性原則。九十年代,大陸一連串的國學熱、文化熱可以放在這樣的脈絡來處理。或者,我們可以說,當代新儒學的滲入正顯示大陸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重新正視,而此中的唯心氣質則代表著辯證唯物論的另一類型的轉進與發展”。[xlviii]
大陸與新儒學對話的另一重要方面,是關於如何認定構成新儒學思潮的代表性人物。這用劉述先的話來說,就是“現代新儒學自梁漱溟揭開序幕之後,已經有了幾個世代的發展。究竟那些人可以包括在這個思潮之內?幾個世代要怎樣劃分?”對此學者有不同意見。大陸的主流意見是方克立的三代人三個階段說,即1920-1949爲第一階段,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馮友蘭、賀麟、錢穆、馬一浮;1950年-1979年爲第一階段,代表人物是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方東美;1980年以後爲第三階段,代表人物是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鄭家棟則認爲,第一代有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第二代有馮友蘭、賀麟、錢穆;第三代有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第四代有杜維明、劉述先、蔡仁厚等。鄭家棟不同與方克立處,主要是把馮、賀、錢作爲第二代,主要理由是馮友蘭雖然只鼻梁漱溟小兩歲,但抗戰時期的學風與20年代差異甚大。劉述先認爲方克立的說法對新儒家的“描述與討論相當全面,頗有參考價值。可惜的是,未能照顧到鄭家棟所提出的論點,乃有所憾”;而鄭家棟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困難。譬如余英時就向我提出,像錢先生和熊先生一向平輩論交,彼此之間並無師承關係,忽然變成了兩代,怎麽說得通呢?”於是,劉述先折衷各家的說法,提出三代四群的架構: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第二群: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他認爲這是到目前爲止,照顧得比較全面的一種辦法。[xlix]這個架構是否恰當,還可以討論,但其作爲兩岸互動對話的産物則是無疑的。
四
在儒學研究中,大陸自1980年代以來一直存在著關於儒教的爭論。熊自健對此作了評述。儒學是否是宗教的討論,首先涉及到如何看待孔子的宗教思想。對於大陸的孔子宗教思想研究,熊自健歸納爲這麽幾種觀點:楊伯峻和匡亞明強調孔子重人道輕天道,只有在個別的特殊場合,“天”才發揮宗教安慰的情感呼應與寄託;馮友蘭和任繼愈認爲孔子保留了西周天命神學傳統,但又對天命的威力作了限制,鼓勵人事有爲,不過馮友蘭突出孔子的道德理念與天命無關,任繼愈強調孔子是從人事活動中去體認天命,天命與人事有爲形成矛盾;北大哲學系與肖箑父主編的兩本《中國哲學史》,把孔子說成命定論者;李澤厚分析孔子仁學結構,以爲儒學既不是宗教,又有宗教的功能,扮演了准宗教的角色;“從大陸學界對孔子宗教思想的新解釋可以瞭解到大陸學界在宗教學領域的學養是有待加強的”,這表現在不能從構成宗教社會的特徵、宗教性超越境界、宗教藝術情懷等來探討孔子的宗教思想。[l]
熊自健還指出任繼愈首先提出儒教說,以爲孔子創立的儒學直接繼承了殷周的天命神學和祖先崇拜的宗教思想,但在先秦還不是宗教,從漢代獨尊儒術起,儒家已具宗教雛形,宋明理學標誌著儒教的完成;並論證了儒教與世界三大宗教的共同性以及獨有的特殊性;對任繼愈的觀點有不少學者提出相反的意見:儒家學說不是從殷周宗教思想發展而來的,而是從西周的倫理道德發展而來的;董仲舒的理論雖有明顯的宗教神學色彩,但在其神學外衣下,仍是儒家的倫理本質;宋明理學沒有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徵,任繼愈說的宗教本質屬性,如教主、經典神聖化、彼岸世界、崇拜物件、神職人員、“罪惡”問題等在宋明理學中也是不存在的。熊自健認爲這一爭論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跳出過去的框框而對儒學進行整體性的辨析”,探索儒學的基本特徵、儒學的多元因素以及這些因素的相互關係,“在學理上將會具有較堅強的說服力”;二是在這爭論中,“最大的癥結在於缺乏一個共同認定的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定義,來判定宋明儒學是否爲一種中國特質的宗教”,因此,“努力去建立一個有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來處理中國宗教問題,將成爲儒教爭論後中共理論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港臺新儒學影響大陸後,新儒學的學者強調他們講儒學的宗教性與任繼愈儒教說的區別:“海外學者傾向于肯定儒學思想有宗教意涵的角度,但那時肯定儒學有它的終極性,乃是與任繼愈完全不同的思路”。[lii]就是說,不贊同任繼愈儒教說的思路。
大陸是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思想的,因此在研究儒學對現實中國影響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儒學傳統的關係自然成爲探討的問題。對此臺灣學者也有所關注。王章陵和曾春海先後列舉了張慧彬、金觀濤、李澤厚、陳衛平、祝福恩等人的論文,並予以評論,前者的評論較爲系統。王章陵把大陸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傳統文化的研究,歸結爲“馬克思主義儒家化”的命題,認爲對這個命題有三種理論詮釋:同構效應論、西體中用論、文化重構論。同構效應論意謂馬克思主義被接受的部分是基於和傳統儒學的文化心理同構,而其與傳統儒學的文化心理不同構的則被排斥了,因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結構上是類似于儒家文化的思想系統的。這一觀點的代表作是張慧彬的《中國傳統文化人文精神的特點》和金觀濤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儒家化》。王章陵主要評論了後者,認爲金觀濤以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爲依據,論證中國馬克思主義是倫理中心主義的思想體系,因而是儒學化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不能把劉少奇要求共產黨員的‘修養’比附到儒家的道德理想,馬克思主義的原質,自始就重視人的立場與品質,絕非劉少奇原創性發展”,而且“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與儒學仁愛哲學毫無‘同構對應’的可能”。對於提出西體中用論的李澤厚,王章陵批評他開始以現代化、馬克思主義爲“西體”,以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現代化與中國實際(包括中國傳統意識形態的實際)的結合爲“中用”,但在後來解釋“西體中用”時,又否認馬克思主義爲體,而謂爲“學”,稱生産方式是“體”;因此,“概念模糊,。前後矛盾”。文化重構論的代表作是祝福恩的《文化重構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出中國馬克思主義經過了中國文化場的重構,因而存在若干變形和失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當反省這樣的變形和失真;王章陵認爲“這當然不失爲挽救馬克思主義危機的法子之一”,但既然馬克思主義和傳統儒學産生于不同的文化場,那麽兩者融合的可能性是很小的。[liii]曾春海也對上述的中體西用論、文化重構論有評論,但大體是重復王章陵的觀點。[liv]
李明輝認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儒家化的觀點不能成立。他指出包遵信、甘陽和金觀濤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貫徹自由化政策的阻礙歸於受到儒家傳統的影響,分別從三個層面來論證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儒家化:包遵信著重於理論思想層面,甘陽偏重社會心理層面,金觀濤強調文化結構層面,但三者“均注意到道德倫理在儒家思想中的優越地位,而將這種特色稱爲‘倫理本位主義’、‘道德理想主義’或‘倫理中心主義’,並視之爲儒家思想與中國共産主義匯合之處”。他主要從儒學的理論意涵來批評馬克思主義儒家化的說法,認爲這種說法的“最大盲點是不瞭解道德與政治在儒家思想中的關係,只憑表面上的形似,便將儒家思想於馬克思主義牽連在一起”;如果借用康得“道德的政治家”與“政治的道德家”的區分,那麽儒家是前者而馬克思主義是後者,就如張灝所說,儒家是政治道德化而毛澤東則是道德政治化,兩者適成對比。他並不否認“在社會心理及文化結構的層面上,儒家的‘德治’思想有被中共假借以爭取支援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之下,上述三位大陸學者的剖析亦非完全無所見”,但是,“不能將這個層面上的探討與儒家思想本身的理論意涵混爲一談,並據此批評儒家。原則上,任何思想都有被假借或歪曲的可能性”,意謂在社會心理及文化結構層面上的儒學,往往是不能代表儒家思想真正意義的。[lv]劉述先認爲金觀濤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儒學化的論證,“主要癥結在於,他仍然未能在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之間作出足夠的分疏,以致陷入泥沼之中。但我覺得,如能補上一些必要的分疏,他的想法仍然是有意義的”;其意義在於指出了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傳統的産物,然而把毛澤東當作儒學化的馬克思主義,則是沒有在概念上加以分疏,因爲毛澤東“完全看不見儒家的超越理想與價值”,金觀濤認爲毛的道德理想主義來自儒家傳統,“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但他所缺乏的是沒有好好討論儒家的理想與精神在馬列框架以內受到的折曲”。[lvi]在李明輝和劉述先看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所受到的傳統影響,並不是真正體現儒學思想精神的東西,因而中國馬克思主義儒學化的觀點無從談起。
以上關於臺灣學者對大陸近二十多年儒學研究述評的歸納,只是以我最近到臺灣一個多月時間裏搜集到的材料爲依據的,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希望批評指正。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 35-37。
[2] 参见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特别见“第六版序言”,第12-20页。
[3] D. C.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Penguin Books, P.73.
[4]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然而,作为哲学变革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同于主流的或正统的西方哲学,而是表现为一种具有深刻哲学意蕴的创造性系统,在世界哲学的发展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i] 郭齊勇:《熊十力思想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77頁。
[ii] 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文本),《熊十力全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卷,第358、200頁。
[iii] 同上,第349-350頁。
[iv] 《馬一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與浙江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一冊,第422-423頁。
[v] 同上,第421頁。
[vi] 同上,第422-422頁。
[vii] 同上,第422頁。
[viii] 同上,第425頁。
[ix] 方東美:《生生之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四版,第3頁。
[x] 參見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三版,第156-160頁。
[xi] 方東美:《生生之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四版,第289頁。
[xii] 方東美:《生生之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四版,第289–290頁。
[xiii] 參見方東美:《中國人生哲學》,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0年版,1993年9刷,第127-129頁。
[xiv] 參見方東美:《生生之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四版,第284頁。
[xv] 詳見牟宗三:《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函義》之《重印志言》,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
[xvi] 同上,第49頁
[xvii] 詳見鄧立光:《象數易學義理新詮─牟宗三先生的易學》,載劉大均主編《大易集述》,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第149-152頁。
[xviii] 岑文載《牟宗三先生與中國哲學之重建》一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245-262頁。
[xix] 詳見牟宗三:《中國哲學特質》第八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0-61頁。
[xx] 詳見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90年,第一冊 , 第300頁。
[xxi] 參見同上 , 第301-302頁.。
[xxii] 同上 , 第304頁。
[xxiii] 參見同上第307-308 , 310頁。
[xxiv] 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貳》,《唐君毅全集》卷十五,臺北:學生書局,1993年,第140-145頁。
[xxv] 同上,第163頁。
[xxvi] 同上,第164頁。
[xxvii]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唐君毅全集》卷十三,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第88頁。
[xxviii] 同上,第83-89頁。
[xxix] 同上,第96頁。
(本文系據2002年11月在臺灣政治大學、輔仁大學講學的內容修改而成,2003年10月改定)
[xxx]此部分的引文均見熊自健《中共學界孔子研究新貌》(文津出版社1988年)的有關章節。
[xxxi] 陳懷恩:《李澤厚〈中國美學史〉孔子部分商榷》,《鵝湖》總第144號,1987年。
[xxxii]李明輝:《解讀當前中國大陸的“儒學熱”》,《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論篇》第98頁,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8年。
[xxxiii]楊祖漢:《牟宗三先生對儒學的詮釋—回應楊澤波的評議》,《儒家思想的現代詮釋》第175-206頁,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年。
[xxxiv] 傅偉勳:《大陸學者的哲學研究評論》,《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第51-52頁。曾春海
的述評見其《以馬列主義中國化爲線索評估中國大陸四十年來的哲學發展》一文。
[xxxv] 鄭宗義:《大陸學者的宋明理學研究》,《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中國大陸與臺灣篇》第123-159頁,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
[xxxvi] 許維萍:《中國大陸宋代經學研究概況》,《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2卷,第3期,2002年。
[xxxvii] 蔣秋華:《大陸學者對清乾嘉揚州學派的研究》,《漢學研究》19卷4期,2000年。
[xxxviii] 李明輝:《中央研究院“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劃”概述》,《漢學研究》19卷第4期,2000年。
[xxxix]李明輝:《中國大陸有關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背景、成果與評價》,《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第175-192頁,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
[xl] 方克立的反批評文章《當代新儒學研究的自我反省—敬答諸位批評者》,《南開學報》1993年第2期,臺灣《當代》第89期轉載;李明輝的回應文章《學術辯論與意識形態鬥爭—敬答方克立教授》,臺灣《當代》第90期。
[xli] 李明輝:《解讀當前中國大陸的“儒學熱”》,《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論篇》第97-98頁。
[xlii] 李明輝:《中央研究院“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劃”概述》,《漢學研究》19卷第4期,2000年。
[xliii] 林安悟:《台海兩岸哲學發展的一個觀察》,《鵝湖》總第316號,2001年。
[xliv] 王章陵:《“新儒學”批判的批判》,《大陸文化思潮》第233-269頁。
[xlv] 劉述先:《論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後現代化的問題》,《大陸與海外》第99-113頁。
[xlvi]高柏園:《再論當代新儒家在外王問題上的缺失》,《鵝湖》總第243號,1995年。
[xlvii] 李明輝:《解讀當前中國大陸的“儒學熱”》,《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論篇》第98頁。
[xlviii] 林安悟:《台海兩岸哲學發展的一個觀察》。
[xlix] 劉述先:《現代新儒學研究之省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2002年。
[l] 熊自健:《孔子宗教思想的新解釋》,《中共學界孔子研究新貌》第45-58頁。
熊自健:《中共學界對儒教問題的爭論》,《中共學界孔子研究新貌》第139-150頁。
[lii] 劉述先:《平心論馮友蘭》,《當代》第35期。1989年。
[liii] 王章陵:《馬學儒化駁議》,《大陸文化思潮》193-230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印行,1993年。
[liv] 曾春海:《以馬列主義中國化爲線索評估中國大陸四十年來的哲學發展》,沈清松主編《中國大陸人文即社會科學發展現狀》,政治大學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出版,1995年。
[lv] 李明輝:《論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儒家化”》,《儒學與現代意識》第45-66頁,文津出版社1991年。
[lvi] 劉述先:《理想與現實的糾結》第122-124頁,學生書局1993年。
酷兒理論 (queer theory)
李銀河
內容提要 酷兒理論是9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一個新的性理論。在過去數年間,一個新的指稱“酷兒”(queer) 從男女同性戀和雙性戀的政治和理論中發展起來。酷兒理論目前是性政治中的活躍分子和學術界十分熟悉和鍾愛的一個理論。
酷兒理論不是指某種特定的理論,而是多種跨學科理論的綜合,它來自歷史、社會學、文學等多種學科。酷兒理論是一種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場:這些人和他們的理論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願意在主流文化中爲自己找位置。“酷兒”這一概念作爲對一個社會群體的指稱,包括了所有在性傾向方面與主流文化和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性別規範或性規範不符的人。酷兒理論就是這些人的理論。“酷兒”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態(nonstraight) 的表達方式。這一範疇既包括男同性戀、女同性戀和雙性戀的立場,也包括所有其他潛在的、不可歸類的非常態立場。本文介紹了酷兒理論的主要觀點和主張,並加以分析。
酷兒理論是一種具有很強顛覆性的理論。它將會徹底改造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使所有排他的少數群體顯得狹隘,使人們獲得徹底擺脫一切傳統觀念的武器和力量。酷兒理論因此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爲我們昭示了新世紀的曙光。
酷兒理論是9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一個新的性理論。在過去數年間,一個新的指稱"酷兒"(queer) 從男女同性戀和雙性戀的政治和理論中發展起來。酷兒理論目前是性政治中的活躍分子和學術界十分熟悉和鍾愛的一個理論。
"酷兒"是音譯,原來是西方主流文化對同性戀者的貶義稱呼,有"怪異"之意,後來被性的激進派借用來概括他們的理論,其中不無反諷之意。我本來想用"奇異"或"與衆不同"之類的詞來翻譯它,但是這樣翻譯過於直白,似乎喪失了這個詞的反諷之意。由於很難找到對應的又表達了反諷之意的中文辭彙來翻譯,所以索性採用港臺的音譯詞"酷兒"。
酷兒理論不是指某種特定的理論,而是多種跨學科理論的綜合,它來自歷史、社會學、文學等多種學科。酷兒理論是一種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場:這些人和他們的理論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願意在主流文化中爲自己找位置。"酷兒"這一概念作爲對一個社會群體的指稱,包括了所有在性傾向方面與主流文化和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性別規範或性規範不符的人。酷兒理論就是這些人的理論。"酷兒"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態(nonstraight) 的表達方式。這一範疇既包括男同性戀、女同性戀和雙性戀的立場,也包括所有其他潛在的、不可歸類的非常態立場。
"酷兒理論"這一概念的發明權屬於著名女權主義者羅麗蒂斯 (Teresa de Lauretis),她是美國加州大學桑塔克魯斯 (Santa Cruz) 分校的教授。酷兒理論最初見於1991年<<差異>>雜誌的一期"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的性"專號。這個理論的發明還有一個小小的故事:首先使用這一用語的羅麗蒂斯是在批評的意義上使用這一用語的。這位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的觀點是:用酷兒理論取代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的提法有一個問題,即掩蓋了二者之間的區別,她擔心這一用語會"解構我們自己的話語和男同性戀者的建構性沈默",這就違背了她提出的強調男女同性戀各自的特殊性的初衷。她還擔心,在酷兒理論以其自身實踐與女權主義理論相區別時,婦女問題,特別是女同性戀問題,會遭到被強制性邊緣化的命運。(Heller,36-37)
關於"酷兒理論"的發明,羅麗蒂斯說過這樣一段話:"有趣的是,魏格曼 (Wiegman)談到了酷兒理論,她正確地將這一用語的發明權追溯到我,那是我爲1990年 (在Santa Cruz)組織召開的一個會議在<<差異>>雜誌上所編的一個專集上首先使用的。她注意到,從那時起,酷兒理論的建立’實際上將差異中性化了’,這一點的確違背我創造酷兒理論這一用語的初衷,我創造這個詞的本意是希望用它來取代無差別的單一形容詞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以便將性的多重性放在它們各自的歷史、物質和語境中去理解。顯然,我是贊同魏格曼的意見的。我也贊同瓦特尼 (Simon Watney) 在一篇文章中的意見。他寫道:目前使用’酷兒’一詞的最方便之處在於,它是性別中立和種族中立的。他又說:酷兒表達了這樣一種立場:它歡迎和讚賞一幅更寬廣的性與社會多樣性的圖景中的差異。"(轉引自Heller,46)
酷兒理論的前身是各種與同性戀有關的理論。羅麗蒂斯認爲,同性戀如今已不再被視爲一種游離於主流的固定的性形式之外的邊緣現象,不再被視爲舊式病理模式所謂的正常性欲的變異,也不再被視爲北美多元主義所謂的對生活方式的另一種選擇,男女同性戀已被重新定義爲他們自身權利的性與文化的形式,即使它還沒有定型,還不得不依賴現存的話語形式。
著名性別和性問題專家威克斯是這樣認識酷兒、酷兒理論和酷兒政治的:從60年代以來登上歷史舞臺的女權運動和同性戀運動可以被解釋爲對當代世界中一種主體形成形式的反叛,是對權力的挑戰,是對個人定義方式、把個人定義爲某種特殊身分、固定在某種社會地位上這種做法的挑戰。"酷兒政治"(queer politics) 是90年代在北美及世界其他地方同性戀中産生的一種新的政治力量。新一代人自稱"酷兒",而不稱女同性戀、男同性戀或雙性戀。"酷兒"意味著對抗——既反對同性戀的同化,也反對異性戀的壓迫。"酷兒"包容了所有被權力邊緣化的人們。
正像"gay"這一用語在60年代打破了舊式同性戀運動中那種自我辯護的姿態一樣,新出現的酷兒政治打破了70年代和80年代同性戀政治的少數派化和整合策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的出現正當同性戀運動成功進入主流文化之時。酷兒政治通過將許多互不相通的成分結合在一起,建造出一種新文化。他們也許是接受後現代主義的當代模式的第一批活躍分子。他們運用舊有和新式的成分建造出他們自己的身分——他們從大衆文化、有色人種社區、嬉皮士、反艾滋病活躍分子、反核運動、音樂電視、女權主義和早期同性戀解放運動中借用風格和策略。他們的新文化是奇妙的,敏銳的,無政府的,反叛的,反諷的。他們絕對認真,但是他們又想從中取樂。酷兒政治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現象,不僅因爲它說了什麽或做了什麽,而且因爲它提醒人們,性政治這一整體在不斷地發明創新,從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Weeks,in Parker et al,45-49)
酷兒理論有哪些主要的觀點和主張呢?
酷兒理論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向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兩分結構挑戰,向社會的"常態"挑戰。所謂常態主要指的是異性戀制度和異性戀霸權,也包括那種僅僅把婚內的性關係和以生殖爲目的的性行爲當作正常的、符合規範的性關係和性行爲的觀點。對於學術界和解放運動活躍分子來說,把自己定義爲"酷兒",就是爲了向所有的常態挑戰,其批判鋒芒直指異性戀霸權。
長期以來,人們以異性戀爲常態,以同性戀爲變態。在20年前,社會還認爲同性戀是某種疾病,人們想給他們治病,想理解他們,或詛咒他們。這不是同性戀者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結構問題。在這種社會規範的統治之下,異性戀者憎恨同性戀者,同性戀者也因爲自己的不"正常"而長期自我憎恨。同性戀恐懼症不再是個人的問題,而成爲社會的問題。70年代活躍的同性戀群體打破了異性戀自然秩序的觀念。現在,異性戀的"自然性"受到了酷兒理論的挑戰,它提出了使性欲擺脫性別身分認同的可能性。
在傳統的性和性別觀念中,異性戀機制的最強有力的基礎在於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欲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一個人的生理性別就決定了他的社會性別特徵和異性戀的欲望。儘管有大量研究證實了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區別,儘管有大量違反這三者之間關係的實踐,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一直沒有受到質疑。儘管根據金西報告,有50%以上的男性和30%以上的女性在一生中曾經有過同性性行爲經驗,異性戀霸權仍舊認爲,性欲的表達是由社會性別身分決定的;而社會性別身分又是由生理性別決定的。
在對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傾向的嚴格分類的挑戰中,巴特勒的"表演"理論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她認爲,人們的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的行爲都不是來自某種固定的身分,而是像演員一樣,是一種不斷變換的表演。在巴特勒看來,沒有一種社會性別是"真正的"社會性別,是其他的表演性的重復的行爲的真實基礎。社會性別也不是一種天生的性身分的表現。異性戀本身是被人爲地"天生化"、"自然化"的,用以當作人類性行爲的基礎。性身分的兩分模式 (彼或此,異性戀或同性戀) 從遺傳上就是不穩定的,這種截然的兩分是迴圈定義的結果,每一方都必須以另一方爲參照系。同性戀就是"非"異性戀;異性戀就是"非"同性戀。因爲對"表演"理論的強調,巴特勒的思想被人稱作激進的福柯主義,它被認爲是一種新的哲學行爲論,其中沒有實存 (being),只有行爲 (doing)。
對於巴特勒來說,根本不存在"恰當的"或"正確的"社會性別,即適合於某一生理性別或另一生理性別的社會性別,也根本不存在什麽生理性別的文化屬性。她認爲,與其說有一種恰當的社會性別形式,不如說存在著一種"連續性的幻覺"(illusions of continuity),而它正是異性戀將其自身在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欲望之間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結果。在異性戀中,這一幻覺靠的是這樣一種假設,即"先有一個生理性別,它通過社會性別表現出來,然後通過性表現出來。"巴特勒反其道而行之,她認爲,異性戀的性統治是生理性別的強迫性的表現。
社會性別表演在下列意義上是強迫性的,即一旦偏離社會性別規範,就會導致社會的排斥、懲罰和暴力,更不必說由這些禁忌所産生的越軌的快感 (the transgressive pleasures),它會帶來更嚴重的懲誡。這一表演帶有緊迫性和強迫性,這一點由相應的社會懲誡反映出來。爲了建構異性戀的身分,異性戀要求一種社會性別的連續性表演。(Butler,19-24)
在巴特勒看來,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欲望這三者之間的聯繫建構了異性戀,而它必定是強迫性的和脆弱的。弗洛伊德所發明的"俄底浦斯情結"是對同性之愛的原初否定。俄底浦斯情結是借用古希臘神話中一位王子殺父奸母的故事來說明,所有的人都有異性戀的亂倫衝動。巴特勒認爲,原初的禁忌並不是異性戀的亂倫,而是同性戀。異性間的亂倫禁忌不是原因,而是禁止同性性欲望的結果。異性亂倫禁忌所禁止的是欲望的物件,而同性戀禁忌禁止的是欲望本身。"換言之,不僅喪失了物件,而且欲望也被徹底否定,於是’我從未失去過那個人,我從未愛過那個人,我真的從未感到過那種愛’。"(Butler,69)
通過剷除異性戀以外的一切欲望,扼殺掉一切其他選擇的可能性,異性戀霸權的社會建構了一種性欲與性感的主體。社會性別的表演將身體的一部分器官性感化了,僅僅承認它們是快樂的來源。在異性戀傾向的建構過程中,人們認爲只有身體的這些部位是用來製造性快感的,社會性別的表演和性活動連在一起:一個"具有女性氣質"的女人要通過陰道被插入而獲得快感,而一個"具有男性氣質"的男人則通過陰莖的插入體驗快感。易性者陷入兩難境地,他以爲如果自己沒有相應的性感器官,就不可能擁有某種社會性別身分。易性者通過植入或切除某些器官以表達他或她的身分,這不是一種顛覆性的行爲,而恰恰反映出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欲望已經被"天生化"和"自然化"到了何等程度。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適當的性別表演上,而不是性感的性活動上。
這一表演就是"社會性別"關於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表演。這種表演使人理解了什麽是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兩分體系。因此,一個男扮女裝的表演並不是對原初形態的模仿,用巴特勒的一句名言來說,它是"一個對模仿的模仿,是一個沒有原件的複製品"。當一個男孩想穿女孩衣服或像女孩那樣生活時,是什麽力量逼著他非要去對自己的身體下那樣的毒手呢?爲什麽他不能夠穿裙子,爲什麽他不能夠簡簡單單地過他想過的女孩的生活呢?這就是因爲他生活在異性戀霸權的淫威之下,一種無形的暴力在規範著他該穿什麽衣服,有什麽樣的作派舉止。這是一種多麽強大又是多麽可怕的力量。它能逼著人殘害自己的肢體。我們簡直不再能把它當成一種無形的力量,它簡直是有形到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程度了。
如果我們接受巴特勒的表演這一概念,使用表演這一尺度,按性身分和性欲的物件來劃分個人的類型就會變得毫無意義。酷兒理論傾向于接受虐戀和其他角色表演實踐,將其違反性規範的越軌行爲定義爲反禁制的性。把酷兒的性建立在一個不斷改變的表演的系列之上,就是對異性戀霸權的挑戰。酷兒理論造成了以性傾向或性欲爲基礎的性身分概念的巨大變化,它也是對於性別身分與性欲之間關係的挑戰。
酷兒理論的第二個重要內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兩分結構挑戰,向一切嚴格的分類挑戰,它的主要批判目標是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思維方法,即兩分思維方法。有些思想家把這種兩分的思維方式稱作"兩分監獄",認爲它是壓抑人的自由選擇的囹圄。
酷兒理論自覺地跨越了各種性類型的尊卑順序,它的中心邏輯是解構兩分結構,即對性身分或性欲的非此即彼的劃分。這個具有反諷意味的概念"酷兒"並不指稱某一種性類型,就像男同性戀或女同性戀這樣的身分,而是指這樣一種過程:性身分和對欲望的表達能夠擺脫這樣的結構框架。酷兒並不是一個新型的固定的"性主體"的標簽,而是提供了一個本體論的類型,它與現代主義話語中的兩分核心相對立。它抛開了單一的、永久的和連續性的"自我",以這樣一種自我的概念取而代之:它是表演性的,可變的,不連續的和過程性的,是由不斷的重復和不斷爲它賦予新形式的行爲建構而成的。
在反對性別的兩分結構 (男性與女性) 的問題上,巴特勒成爲最有權威的理論家。跟隨福柯的理論脈絡,她向固定的女性身分的必要性提出質疑,探索一種批判各種身分分類的激進政治的可能性。她向性別和性欲的內在能力、本質或身分的概念提出質疑,認爲它們不過是一種重復的實踐,通過這種反復的實踐,"某種表像被沈澱、被凝固下來,它們就被當成某種內在本質或自然存在的表像"。"欲望的異性戀化需要’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的對立,並且把這種對立加以制度化,把它們理解爲’男性’和’女性’的本質。"(轉引自Segal,190)
在酷兒理論對各種身分分類的挑戰中,超性別 (transgender) 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謂超性別包括異裝和易性,還包括既不異裝也不易性但是喜歡像另一個性別的人那樣生活的人。巴特勒認爲,男女兩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生理學統計表明,世界上有6%至10%的人天生就處在兩性之間,他們的生理性別是不確定的。
兩性界線不清和有越來越模糊趨勢的表現在當今世界隨處可見,正在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時尚。
在悉尼,打破兩性界線的人們舉行了一日的遊行,有成千上萬的"正常"人看到了他們。
美國的麥可·傑克遜是貓王以後最著名的歌星,是彼得·潘以來最著名的男女同體的民間英雄。他的存在是對男女兩分觀念的威脅。
英國的辛普森 (Mark Simpson) 在大衆傳媒中爲人們提供了一個最新的同性戀色情明星、被動肛交者和性受虐者的詼諧的公衆形象,他的形象出現在從足球和健美到關於去毛和男褲的廣告當中,他的形象說明,男性身體——裸露的、被動的、作爲性感物件而被人渴望、被人觀賞的——開始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被展露出來,他說:"傳統異性戀的觀念在這種顛倒面前已難以爲繼。"(Segal,198-199)
除易性行爲外,異裝行爲也是超性別中一個重要的形態。異裝行爲的一個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是對兩分的簡單概念的挑戰,是對男性和女性這種分類法的質疑。
超越性別角色這一社會潮流中的另一個重要形式是男角的女同性戀者和女角的男同性戀者,他們的存在使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傾向的全部定義都成了問題。這兩種人的自我社會性別認同與生理性別不符,他們的生理性別是男性或女性,而他們的社會性別認同是另一種性別。他們的性傾向也與生理性別不符:在心理上是異性戀的,而在生理上卻是同性戀的。
進入90年代,超越性別和性別角色的模糊化有愈演愈烈之勢。在某個心理診所,一個女孩向醫生描述自己所遇到的問題:她想做一個男性,而且是一個同性戀男性。也就是說,她的生理性別是女性,她的社會性別是男性,她的性傾向是同性戀。她是女人,她愛男人,但是她不想作爲一個女人來愛男人,而是作爲一個男人來愛男人。這就是90年代人們所面臨的新局面。
伯恩斯坦 (Kate Bornstein) 在1994年說:對於"誰是易性者"這一問題的回答完全可以是這樣的:"任何承認這一點的人。"一種更政治化的回答是:"任何人——他的社會性別表現從社會性別結構本身看來是有問題的。"(Beemyn et al,35) 對此,巴特勒有一句名言:每個人都是易性者。她是指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成爲一個標準的典型的"男性"或"女性","同性戀者"或"異性戀者"。
對於超性別現象的重視,使得雙性戀傾向在酷兒理論中擁有了特殊的重要性。酷兒理論認爲,自由解放的新版本就是取消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區別;如果實現了這一變化,所有的人將不得不承認他們自己的雙性戀潛力。雙性戀之所以有著特別的重要性正是因爲,雙性戀者的存在本是就對"正常人"、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的區分質疑,雙性戀的形象就是一個重要的越軌的 (transgressive) 形象。雙性戀能夠解構社會性別與性的兩分結構的原因在於:首先,因爲雙性戀佔據了一個在各種身分之間曖昧不清的位置,所以它能夠昭示出所有身分之間存在的缺陷和矛盾,表明了某種身分內部的差異。其次,因爲身分不定,雙性戀揭示出所有政治化的性身分的特殊性質:一方面是個人性行爲和情感選擇隨時間不同的巨大不連續性;另一方面是個人政治身分的不連續性。
目前,有些酷兒已經幽默地自稱爲"彎曲的直線"(straight with a twist)。"直線"本是英文中"正常人"或"異性戀者"的通俗說法。"彎曲的直線"這種說法充分揭示了各種分類界線之間正在變得模糊起來的新趨勢。將來,我們會有彎曲的直線,會有搞同性戀的異性戀,會有具有女性氣質的男人和具有男性氣質的女人。一位學者打趣地說:"誰知道呢,也許在明年的學術研討會上,我們會看到這樣的論文標題:女同性戀的異性戀——最後的未知領域。"(Heller,47)
第三,酷兒理論還是對傳統的同性戀文化的挑戰。酷兒理論和酷兒政治預示著一種全新的性文化,它是性的、性感的,又是頗具顛覆性的,它不僅要顛覆異性戀的霸權,而且要顛覆以往的同性戀正統觀念。酷兒理論提供了一種表達欲望的方式,它將徹底粉碎性別身分和性身分,既包括異性戀身分,也包括同性戀身分。
英國背景的瓦特尼 (Watney) 和美國背景的沃納 (Michael Warner) 將酷兒政治定義爲僞裝神聖的道德主義的男女同性戀身分政治的對立面。瓦特尼指出,傳統的同性戀身分政治爲了向人們對同性戀的刻版印象和熟視無睹挑戰,有一種以"同性戀社群價值"的名義壓抑在酷兒性行爲中大量存在的差異的偏向,因此創造出一套關於同性戀生活方式的高度正規化的圖景。相反,酷兒文化是對這種高度正規化的同性戀價值的否定,其性多樣化的圖景囊括了從奧斯卡·王爾德到芬蘭的湯姆 (Tom of Finland),甚至包括麥當娜這樣的人。瓦特尼宣稱,酷兒文化是對"占統治地位的性認識論權威"的挑戰。
酷兒理論抨擊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分別,揭露和批判了這種兩分論的隱蔽的運作方式。酷兒理論家司德維克 (Sedgwick) 是這樣解釋的:某種文化中兩極對立的分類,比如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劃分,實際上是處於一種不穩定和動態的關係之中。因此,僅僅爭取對同性戀的正面評價是不夠的,還要保護人們選擇做酷兒的權利。
酷兒理論向男女同性戀身分本身質疑,批評靜態的身分觀念,提出一種流動和變化的觀念。酷兒理論嘗試將個人身分政治轉向意義政治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酷兒理論不把男女同性戀身分視爲具有固定不變的內容的東西,而將身分視爲彌散的、局部的和變化的。對於一些人來說,身分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動關係和角色變換創造出來的。酷兒理論批判了傳統同性戀理論在身分問題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構男女同性戀身分的嘗試中,異性戀是如何被正規化的。
第四,酷兒理論具有重大的策略意義,它的出現造成了使所有的邊緣群體能夠聯合起來採取共同行動的態勢。酷兒理論相信民主原則在個人和個性的發展中也同樣適用。酷兒政治建立了一種政治的聯盟,它包括雙性戀者、異性者、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以及一切拒絕占統治地位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體制的人。酷兒政治接受所有認同這一新政治的人,不論他們過去有著何種性身分、性傾向或性活動。嚴格地說,一個人既不能成爲一個同性戀者,也不能是或不是一個同性戀者。但是一個人可以使自己邊緣化,可以改變自己,可以成爲一個酷兒。
"酷兒"一詞因此具有策略性的意義,而不是指稱某種具有永久性意義的身分。酷兒性(queerness) 並不是一種新的身分,這一概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爲這些人們擁有共同的經驗,他們共同作爲性越軌者 (sexual outlaws) 的生活方式,而並不是一種這些人共同擁有的本質主義的身分。它出現在那些孤立的個人當中,與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價值相對立,與異性戀霸權相對立。
許多酷兒活躍分子不再將自己定義爲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甚至不說自己是異性戀者,而簡簡單單單地自稱爲酷兒。酷兒的性活動很難在傳統的性結構領域中加以定位,它是一些更具流動性、協商性、爭議性、創造性的選擇。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也許需要"走出來",但是酷兒身分卻是"走進去"的。酷兒還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分類方式:酷兒,較酷兒,最酷兒 (queer,queerer,queerest)。這種分類方式與以往的任何分類方式都不一樣。
酷兒理論的多重主體論 (multiple subjectivities) 造成了在不同社會和種族的歷史背景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不連續性 (discontinuities),爲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超性別者、易性者和雙性戀者的社群之間更強有力的聯合,爲他們改造制度化的異性戀霸權的共同努力創造了條件。
最後,酷兒理論與後現代理論的關係。酷兒理論出現于後現代思想盛行之時,與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酷兒理論的哲學背景是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理論。後現代理論是遇到最多誤解的理論,例如,它常常被人們誤解爲要取消一切實際行動和現實鬥爭。因爲它解構了所有的"宏大話語",解構了所有的分類和身分,因而取消了所有現實鬥爭的可能性。
有些女權主義者就持有這樣的觀點,她們認爲,女權主義不可過於投入後現代主義的懷抱,這是與敵同眠。她們認爲,後現代主義是社會變革的敵人。這種態度與女權主義對酷兒理論的複雜感覺有相似之處。其實,這種恐懼和擔憂是建立在對後現代理論的誤解之上的。後現代的解構主義不過是一種模式轉換而已,它並沒有使任何事物變成"暫時的"或"不真實的"。認爲"男性"和"女性"、"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作爲一種身分的劃分是不正確的,並不會使它們因此變得"不真實"。實際上,它對於反抗壓迫的鬥爭是極爲有益的,它可以使人們獲得一種擺脫現存的僵化的社會文化機制的力量。
後現代理論家威爾頓說:"我甚至要說,對於女權主義來說,性別的解構和重寫 (這一重寫可能採取徹底取消性別的形式) 的唯一選擇是消滅男性!無論性別是一種壓迫性的操縱性的結構,還是男人’天生’要壓迫女人,女人是’天生’的受害者,全都應當被掃除乾淨。"(Wilton,in Adkins et al,108) 取消或者說解構"男性"和"女性"、"同性戀"和"異性戀"這些概念,並不像有些女權主義者所想像的那麽可怕,並不會取消現實的解放鬥爭實踐,而是爲這一現實鬥爭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提供了一個新的武器。
酷兒理論是一種具有強大革命性的理論,它的最終目標是創造新的人際關係格局,創造人類新的生活方式,它的做法是向所有的傳統價值挑戰。
它向傳統的家庭價值挑戰。一位酷兒理論家說:"我認爲,傳統的家庭價值不會延續到下個世紀,隨著人的壽命增加,我不相信人們能保持50年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生活。我想我們會找到某種既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是通姦活動的生活方式。"(Grant,267)
它向傳統的性別規範和性規範挑戰。對於酷兒來說,他們的亞文化爲他們提供了廣大的有意識的表演性的性與性別角色的天地,他們可以從男性角色變爲女性角色,從異性戀角色變爲同性戀角色。對於一個酷兒來說,即使是一個有易性傾向的人,也沒有絕對的必要做變性手述,按照酷兒理論,他完全不必受這個罪,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完全不必一致,想穿哪個性別的衣服,就穿;想過哪個性別的生活,就過;想做哪個性別,就做,不必要先改變第一性征才有資格做某種性別的人。按照酷兒理論的理想,在一個男人不壓迫女人的社會中,性的表達可以跟著感覺走,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分類將最終歸於消亡;男性和女性的分類也將變得模糊不清。這樣,性別和性傾向的問題就都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酷兒理論是一種具有很強顛覆性的理論。它將會徹底改造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使所有排他的少數群體顯得狹隘,使人們獲得徹底擺脫一切傳統觀念的武器和力量。酷兒理論因此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爲我們昭示了下個世紀的曙光。
從境界的維度解讀當代意義上的形而上學
陸傑榮
內容提要:人的本性從實質上而言是某種具有超越指向的形而上存在,哲學的本質與人的本性的一體性關聯體現在哲學總是從構建某種理論樣式的“形而上學”以表現人在某一特定生成階段中的形而上旨趣。從這個意義上說,哲學總是通過“境界”的方式來表達著人的形而上追求,印證著或物件化爲不同理論式樣的“形而上學”。從哲學境界的維度出發,可以更好地把握形而上學發展的內在邏輯,更好地直觀人的形而上本質,更好地構建當代意義上的形而上學,更好地洞曉時代精神精華的內蘊。
(一)
人從本質上而言乃是具有超越指向的形而上存在。如海德格爾所言,人生而具有形而上的天性。“一方面人具備種種能力,一方面他也有所欠缺”。[lvi]人具有這種能力,對自己存在的種種欠缺提出追問。同人的超越性質相吻合,各門其他學科的物件是給定的,哲學探索的物件不是給定的,而是未定的,這就注定了哲學永遠在追求著它所設定的物件,或在給定物件之外去“創造”它的物件。形而上學乃是人自身的需要。“神無所不知,其他動物一無所知;只有人,只有人才知道自己有所不知”。[lvi]
人的形而上學本性根源於人的自身矛盾。人要超越這一矛盾,通過形而上學的追問以超越自身分裂性存在的局限性。形而上學是人消解自身矛盾乃至人和世界矛盾的自我意識表達方式,這就從一個側面進一步印證了哲學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人的分裂(分化)是形而上學的“根”,對這種分裂性存在的思考既是“原初”的思考,又是“終極”的思考。當人對這類問題進行思考時就是在“返歸”(黑格爾語)或“傾聽”(海德格爾語)形而上學。
從實質上說,現代哲學反對形而上學只是力圖否定在歷史中曾經有的那種形而上學,換言之,它們批判的只是形而上學的一種方式,而不是反對形而上學本身。現代哲學在反對特定形而上學某種方式的時候,也從反面說明了形而上學的不可消除性。有人存在,就有形而上的思考。
形而上學是對人本性分裂的反思,這意味著形而上學就是追尋,它面對著徹底的、整體的疑問。形而上學是沒有答案的問題。問題比答案更重要;即使有答案,它本身仍然是問題。形而上學又是對人分裂後統一的反思,這就是說人總要在追尋中確立終極的問題,雖然這只是相對“終極的問題”。當人在進行形而上學思考的時候,人也就進入了哲學的境界。哲學境界始於形而上學的追尋,終於對形而上學的解答。“從這個意義說,形而上學的追尋——即人的最終的命運——本身就包含著極大滿足的可能性,確實,在某些歡悅的瞬間,也包含著一種完滿性。這種完滿性絕不依存於任何可公式化的知識,教義和信條,而是依存於人的本質的一種歷史性的實現。……哲學的力求的目的在於領悟人的現實境況中的那個實在(reality)。”[lvi]形而上學是對問題的追尋,又是在追尋中獲得的“完滿”。
形而上學既然是人的本性,就表明人具有確立哲學境界的內在的要求。但已經成爲“歷史”的形而上學不再是形而上學。歷史的形而上學已是“事實”,形而上學實質上是對未來的“設計”,不斷出場的“設計”,這就是現代哲學所說的“哲學終結”、“形而上學已經完成”的真義所在。形而上學的“meta”不是如亞裏士多德所說的是在知識之後的“神聖學術”,依此方式建立的形而上學雖然也包括著各種“設計”,但都是規定好的“事實”設計,它實質也是“事實”,形而上學的本意是超越,“meta”不是在……之後,應是對……超越。因而,形而上學是人的本性,著眼點在於人總要在現存的境況下對“未來”有所“設計”,這就是人的形而上學。以往的形而上學是無“時間化”、“方位化”的形而上學,具有“永久”的“現時性”特徵,一切都固定化了,被設計好了。這種形而上學也包含著“未來”,但已是“事實”的“未來”,“未來”仍是確定化的“事實”。
傳統的形而上學是“事實”的形而上學,隨著“事實”從形而上學中分離出去,形而上學似乎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形而上學的性質是“超事實”,因而就要從“事實”之外去尋找。這樣,時間、未來、設計的規定就要引入形而上學。當這樣的背景框架確立之後,哲學的定位起點同樣是形而上學,但已不是“事實”的知識,而是超越“事實”的境界了。現代的形而上學更能超越其他事實性的知識,體現形而上的性質。在這個意義上說,哲學境界就是現代的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的本性首先表現爲人的提問。驚異、畏懼、質疑、釋義都是在提問。人的追問的無限度性恰是形而上學的標誌。在人的追問中,被追問的物件就從表像進入到非表像層次,就從“可說”的世界進入到“不可說”的世界,這就是說人在對“事實”命題的追問中總要推出“非事實”的知識,這是形而上學本身的性質。形而上學採用表徵的方式回答其所提出的問題。表徵方式不是知識、概念、範疇的表達方式(知識的表達總是體現爲思維結構與實體結構在一致性基礎上的邏輯陳述),表徵方式的意義說明哲學的物件不是指稱性的,而是表徵式的。表徵方式之所以適用於形而上學,因爲它既不同於知識的指稱方式,也不同於宗教的象徵方式,它包含著意指和意謂的統一,在這二者的統一中,哲學的形而上學更強調對“意指”的超越,對“意謂(意義)”的推崇。現代形而上學應是確定意義的自我意識表達方式。
那種把形而上學等同於“有形”知識的觀點在歷史中曾經有自身存在的根據,但是從現代的角度看又是錯誤的。形而上學並非“有形”東西的組合,以此構成的本體論至少背離了形而上學的本意。形而上學不是“有形之學”的本體,簡單將形而上學看作知識,哪怕是最高智慧的知識,也是片面的。當“有形”的東西從形而上學剝離出去後,形而上學的地位就受到了巨大的衝擊。那種簡單地將形而上學等同於“無形”世界的看法也是錯誤的。“無形”即上帝的存在,這就將人的形而上學性虛幻化爲“無形的”(非人)的東西。形而上學是“無形的”,它是基於“形”又超越“形”的(形而上),但它又是“有形的”,可以理解和確立的,這可以說是人所獨特具有的“意義”。形而上學是從人的角度去看人,看物件時候所産生的既涵蓋物件又超越物件的意義,也是人從未來角度設計的時候給自己生活的統一性提供的“意義”。“設計”是不斷進行的,“意義”是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意義”就是對舊的“設計”的批判,“意義”總是被“超越”的,哲學境界從這個角度說就是形而上學所提供的“意義”。
依據人的形而上學本性,對哲學境界的現代解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人的實踐活動將世界二重化,人的應然邏輯將生活二重化,人的形而上學本性則將意識二重化。人總是在兩個不同層次的意向性維度上將意識加以分離:其一是對“物件”的意識,其二是對“物件”意識的意識,後者也可以被看作超越物件意識的意識。如果說實踐活動是人將世界、生活與意識雙重化的前提和基礎,那麽意識的兩重化,特別是超越物件意識的意識的形成,恰好表現了人在何等程度上遠離自然界,表現了人在何等程度上將自然“虛無”掉的,表明了人在何等程度上更具有人性性質的。超越物件意識的意識就是形而上學的思考內容,超越物件意識的意識提供的意義就是哲學的境界。這樣,基於形而上學之上的哲學境界對人來說就有了最爲緊要的不可替代的價值。
(二)
馬克思從當代哲學的意蘊上指出解釋世界只是以往哲學家的事情,這是因爲古典哲學家終究是哲學家,他們無法借助於哲學理論給世界帶來變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以往哲學家是軟弱無力的,哲學家所確立的境界也是空泛的。然而哲學家的軟弱卻不能印證哲學的無能。也正是基於這一前提,才可以說,馬克思並不是哲學家(舊有意義上的),他不訴諸純然對世界的解釋,雖然這一解釋是多種多樣的,而是要使哲學能夠産生“真實的結果”。“真實的結果”的哲學,儘管根植于現實的物質條件之中,但絕非“現實”的複現或描述,而是說“任何真正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舊有的哲學在這個意義應該消除,同時應該創立一種全新的哲學。馬克思強調哲學給世界帶來變化是以哲學的“真實”,以不損害哲學固有的特定功能爲前提性條件的。哲學訴諸對世界的解釋是必要的,但這種解釋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批判性”的、“評價性”的,哲學顯然要超越于現實的描述層次,而提供在非哲學的現實活動基礎上確立並與歷史發展條件相吻合的關於世界觀層次上的理論支援,哲學自然要有境界問題。在這樣的規定意義上說,馬克思並不一概反對康得把哲學看作是人安身立命之本的比喻,問題的實質在於馬克思認爲不存在著超越歷史之外的這樣的安身之命根據。因此,馬克思在將哲學返歸於現實的同時,對哲學的境界提出了論理縝密的辯護。在馬克思看來,道理十分明確簡單,未來的世界不會是其他什麽樣性質的世界,而注定是哲學的世界,這樣馬克思就肯定了哲學在人的同實生活乃至精神生活中的價值和意義。
馬克思的解釋意味深長。哲學的境界從消極意義上說是指哲學的批判性、否定性,不承認永恒的存在,將事物現象從暫時性方面加以理解;從積極意義上說又是指哲學的建構性、導向性和矯正性。哲學並非是“可有可無”的,而是“至關重要”,甚至“舉足輕重”的。對“那些以爲哲學在社會中的地位似乎日益惡化而爲之歡欣慶倖的可憐的懦夫們”,馬克思說道:“哲學,只要它還有一滴血在它的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中跳動著,就會表現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lvi]無論社會怎樣發展,總是需要有人成爲“哲學的日曆中最高尚的聖才和殉道者”。
馬克思經常這樣問題:人不是“一直努力想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創造自己的真實存在”嗎?馬克思在這裏用詞極爲嚴謹,至少表達了三重要互關聯的含意:其一,人有其真實存在的規定;其二,人的真實存在是創造出來的;其三,人的真實存在有關階段性的區別。馬克思這一論點的邏輯是一貫的。馬克思十分讚賞黑格爾關於“否定性勞動”對自然向人的生成的意義,認爲必須把事物、現實、感性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在理解。這樣,世界的一切關係都是爲我關係的存在,所謂爲我關係的存在(The Being for myself)就是從人的自身的方面,從人的超越方面來看“物件”,不是把自然(物件)看作沒有人的痕迹的無的東西。“抽象的孤立的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來說是無”。[lvi]自然對人的生成的否定性就意味人不斷賦予能者多勞明以人的規定,不斷超越既定的規定的內容。這樣看來,“所聞所謂的世界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的誕生,是自然對人的生成”。[lvi]人在更高水準上重新創造自己的真實存在與自然向人的生成是一體的歷史過程,顯而易見,馬克思是從人的歷史與歷史的人統一高度來審視哲學的境界意義的。
馬克思從人的生成層面提供了對哲學境界理解的尺度。在馬克思看來,人和動物有著明確的分界,人具有否定物件的勞動本性和分化物件的實踐本性,“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物種的尺度和需要來進行塑造”,動物的活動是“承襲”、“複製”,人的活動是“超越”。哲學可以說是“超越”性的精神表達方式。馬克思地一步分析:人則懂得按照任何物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産,並且隨時隨地都能用內在固有的尺度來衡量物件;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馬克思提出了兩個尺度對哲學境界的理解尤爲重要。
從第一個尺度看,人是按照任何物種尺度進行著生産,人是什麽是和他們如何生産相一致的。這一尺度表明人怎樣的生活,必須通過客觀物件化的生産活動加以印證,人的本質借助於這一客觀物件性的活動表現出來。
從第二個尺度看,人又每時每刻用“內在固有的尺度”“衡量”物件,所謂內在固有的尺度就是指人性的內在尺度,而“衡量”物件的尺度決非存在於物件之中,因而是超越物件化的活動的,對“物件”的“衡量”可以包括肯定、否定、批判、矯正等等,因而馬克思所說的“內在固有尺度”乃是哲學上的,是人按照“內在固有的尺度”構建衡量“物件”的根據、前提,這些都可以構成哲學境界所包括的內容。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爲什麽說古希臘藝術和史詩給人們的精神享受在某方面說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爲什麽說與物質生産相分別,社會還需要自由的(精細)的精神生産,爲什麽說現代雇傭勞動的特徵就是人性精神的喪失,爲什麽說“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産領域的彼岸”。[lvi]人的生成不能離開人具有的“內在固有”的尺度,不能借助於外在規定加以限制,它是自由的、全面的、完整的,也就是說,作爲一個完整的人,佔有自己的全面本質。馬克思的問題有了哲學式的結論,人通過兩種尺度進行著“生産”,努力想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創造自己的真實存在。由此可見,馬克思從哲學境界的維度提出了當代意義上的形而上學問題。
(三)
從當代的時代精神境遇與旨趣來看“形而上學”的話,就會看到“形而上學”有其邏輯自身的展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必然地會體現出自身的特點與性質。從歷史的發展過程考察,“形而上學”最初體現爲“物件”,所謂“物件”就是體現爲一個“世界”,儘管這一“世界”是“概念”的世界,而且這一“概念”世界還制約著、決定著現存的“感性”世界。這一“物件”是人所創造的,體現著人的追求,人的價值注入與人的意義構建。人所創造的這一“物件”既然是外在於人的,它就會或多或少成爲人的“異在”,成爲制約人,限制人甚至壓抑人的某種“物件”。正因爲如此,人要通過將這一“物件”置放於主體性批判的審視之中,對“形而上學”給予新的詮釋。這就是說,人要將“形而上學”用新的檢驗方式加以重新“整理”,以便使“形而上學”轉變某種形式,進而適應於人本身的精神發展的需要。與這一特點精神發展的客觀邏輯相對應,對“形而上學”是什麽的“What”這一本質主義的理論追問必然演變成爲對“形而上學”是“如何”(可能)的“How”的探討。而這一探討既然在近代哲學的主客二元模式內所展開,“形而上學”的“事實”與“價值”的對立仍然處在不可擺脫的理論矛盾之中,二者的衝突蘊含著對“形而上學”問題給予解決的不同進路。科學的反形而上學潮流從經驗的有限性思維出發,必然將“形而上學”的內容消除,而保留其表像思維所固有的形式訴求,非科學的反形而上學潮流則力求從“形而上學”所被“遮蔽”的因素著手,將人與“形而上學”看作是一體的規定。用海德格爾的觀點表述,“形而上學就是人的本性”。“形而上學”在“終結”的反對聲中並沒有煙消雲散,而是變換了“位置”,使其同人的本性的內在關聯開始澄明起來。
深入地說,“物件”的“形而上學”是籠而統之的“形而上學”,它包括了繁雜的內容,從實質上看是將“事實”與“價值”的東西混雜在一起,沒有“分化”,沒有“差異”,只是一種“混合”。“方法”的“形而上學”力求實現某種“劃界”,這就是將“事實”的東西歸入“事實”,將“價值”的東西隸屬於“價值”,“形而上學”經過“批判”的“辨別”被分割爲不同的,甚至互不相通的領域。“事實”與“價值”形成了“對立”,二者變得“格格不入”甚至對立起來。而“形而上學”從品位上而言乃是強調價值、意義因素的重要性,雖然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容納“事實”的東西,這樣新的“形而上學”不是抹殺“物件”,排斥“方法”,而是在批判性地保留之中,將“形而上學”定位於一定的“視界”之內。換言之,“形而上學”不是永恒的“物件”,也不是絕對的“方法”,而是在特定的“視界”之中所觀察與提升的“形而上學”。我把這種類型或樣式的“形而上學”叫做“視界”的“形而上學”。
“視界”的“形而上學”從其特有的性質而言,強調了“形而上學”不是某種“知識”,不是某種“物件”,而是看問題的一個層面、一個維度。“形而上學”的“物件”是一個“世界”,雖然與人相關,但這一“物件”與人的相互關係不是一個互動的關係,而是從“世界”至上的單向維度看待人,所以它對人來說,是一個外在的不可擺脫的“限制”;“形而上學”的“知識”是板結的、固定的、沒有變化的“知識”,具有“永恒”“絕對”,而沒有“時間”因素的滲透,這種“知識”有邏輯,但沒有“快樂”(尼采語),有權力,但沒有“釋放”(福柯語)。“視界”的“形而上學”從時間的“地平線”(海德格爾語)啓步,不是用“時間”解構或“磨平”形而上學,而是在時間之中去審視“形而上學”,將“歷史的絕對性”與“時代的相對性”二者結合在一起,構成特定視界內的“形而上學”。在這個意義上說,它反對“物件”的“形而上學”的絕對主義立場,又不落入相對主義的困境。它訴諸於“事實”,但決不停留於對“事實”的實證分析,而是在“超越”事實的基礎上,側重對“事實”考察價值尺度的優先性理解。
“視界”的“形而上學”從其理論的指向而言,提供了研究人本性的新角度。“形而上學”從本真意義上來說,是對人本性的研究與反思,人乃是形而上的存在,哲學乃至“形而上學”從要義上是對人的本性的尋問與解答。人總是在特定的境遇之中去面對“形而上學”問題,又總是在特定的維度內回答“形而上學”的問題。這表明,人對“形而上學”的尋求與解答都是在“視界”內完成的。“形而上學的追尋——即人的最終的命運——本身就包含著極大滿足的可能性,確定在某些歡悅的瞬間,也包含著完滿。這種完滿性絕不依存於任何可公式化的知識,教義和信條,而是依存於人的本質的一種歷史性的實現。……哲學所力求的目的在於領悟人的現實境況中的那個實在(reality)。”現實的境況與歷史性的因素既然被納入到對“形而上學”理解的要素之中,那麽自然就構成了“形而上學”理解的“視界”。從“視界”的角度可以理解人的本性在歷史的不斷展開過程,進而也可以理解與人的本性展開相適應,“形而上學”的表達內容也是在歷史的“視界”中所實現的。
“視界”的“形而上學”從問題的實質而言,表達了與人的精神品位相對應的哲學境界。事實上,“形而上學”作爲人的精神表達的自我意識方式,其運思指向與根本目的是構建表達人的本性的哲學境界。柏拉圖認爲,人的天性就具有哲學的成份,其意蘊在於表達人總是通過“超越”“自爲”的本性來表達其精神境界。“形而上學”通過哲學的境界以表達人的本性要求,而反之哲學境界是以“凝煉”的方式體現了“形而上學”與人的本性的內在一體性的關係。“哲學就是這樣一種適應於人的特有本性,以反思意識的獨特方式表現人對自身的存在性質、生存意義、生活價值的理解和對人的未來前景,更高發展,理想境界的追求的特有意識形式。”人的本性的昇華主要是通過“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價值世界的構建,更進一步說,借助於哲學境界提供的世界圖景,借助於人對生活意義的終極關懷,借助於對人活動的整體性意義的把握來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視界”的“形而上學”從當代時代精神的角度顯現了其內在具有的本真意蘊,昭示了哲學與人的內在關聯性質。
綜上,當代意義上的“形而上學”提供了理解人的本性的“視界”,在這一“視界”內,“形而上學”不是外在於人的“世界”,而是人生存的“世界”(視界);“形而上學”不是從知性認識方式出發所形成的“知識”,而是人得以對自我反思的一個“維度”;“形而上學”不是從“事實”經驗層面所構成的“當下”在場,而是人將“事實”置於否定性關係之中的肯定因素的確認(理想)。與以往的“形而上學”相比,“視界”的“形而上學”是相對的,因爲它在“時間”之中,在“歷史”之中;與同時代的知識表達方式的特點相比,它又是“絕對”的,因爲它是相對於同時代而言的歷史中的“絕對”。
參考主要文獻:
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上下卷
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
黑 格 爾:《邏輯科學》
羅 蒂:《後希望形而上學》
懷 特 海:《思想方式》
狄 爾 泰:《精神科學引論》
雅斯貝斯:《智慧之路》
如塞爾:《什麽是哲學》
深刻變化的世界與當代中國哲學的使命
趙劍英
內容提要: 當今社會是一個交往普遍化和緊密化的“全球化社會”,是一個由資訊化網路化數位化爲構造機制的“技術化社會”,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的“風險社會”,是一個民族國家主權正在在削弱、“世界公共社會空間”日益增長的“跨國社會”,人的存在也正在日益成爲“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歷史的人”,即“世界公民”。所有這些都表明著人類社會形態正在發生深刻的巨變。
面對全球化趨勢和技術化社會,面對深刻變化的世界,當代中國哲學的現狀如何?當代中國哲學應有何作爲,應向何處去?這是擺在當代中國哲學研究者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長期以來,在中國,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倫理學等學科間互不交流、對話,甚至相互輕視,作爲愛智的哲學卻成爲被肢解和分裂的哲學,哲學家也成爲片面化的、“專業化”的“哲學工作者”。學科體制和學術評價制度以及教學方式的不盡科學合理更強化了這種不正常現象。這樣的哲學顯然無法回應時代的問題,更遑論肩負起指導人們改變世界的使命。
因此,對於中國哲學來說,必須積極倡導和推動哲學各學科間的交流和對話,實現方法、視野的互補和相互激蕩,從而實現思想的提升和創造。
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最鮮明影響最深遠的特徵無疑是全球化、資訊化和網路化,人類社會形態及運行發展機制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所謂全球化就是由於資本的全球擴張和資訊技術的迅速發展及廣泛運用,使人類不同主體間的交往日益普遍化和緊密化,這真正是一個馬克思早就指出的由“民族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普遍交往”時代,人類交往的迅時性、關聯性、互動性、開放性大大增強,交往的效率大大提高,交往的成本大大降低,可以說,資訊運動已成爲物質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基本方式,這將進一步促進人類生産、流通和消費的互補互促效應以及各自效率的提高,表明了社會的進步。
全球化、資訊化社會也是一個技術化社會。當代社會交往和社會組織結構體系是以資訊、衛星、電信等一系列現代技術爲手段和基礎構建的。人們的交往物件、實踐和認識活動物件日益資訊化,社會組織日漸網路化,高新技術在社會生産和社會生活中的運用越來越廣泛而深入。
技術社會無疑是人類生産力和生產關係的的巨大躍遷,然而它也對人的存在狀況和境遇正産生著極爲重要的影響。“技術的變革正逐步推翻著我們的時間觀,我們對遠近空間的看法,以及我們對世界的描述,同時也造成了人們新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lvi] 在這種新的技術社會中,人不僅越來越依賴於技術,離不開技術,適應技術的要求,爲技術所統治,而且越來越生活在符號性的人工景像世界中。鮑德裏亞等後現代主義者深刻揭示了當代社會的基本特徵:科技化、虛擬化、媒體充溢、消費主導,指出人類正生活在一個“仿真”的世界,在這個社會中,實在與影像之間的差別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審美的方式呈現出來,也即出現了仿真的世界或後現代文化[lvi]。憑籍資訊技術、網路技術和電子媒體,人類正生活在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轉換之中。“從印刷人時代走向圖像人時代這一步,是由於照相術的發明而邁出的。”[lvi]如果說照相術的問世只是現代文化圖像化、視覺化的開端,那麽虛擬技術的出現則爲圖像文化的興起提供了得心應手的技術基礎。“數位圖像不只是圖像製作史上的又一項新技術,它還是一種新的書寫方法,可以與印刷術的發明和字母表的誕生相提並論”[lvi]。“不能低估圖像文化,尤其是動態圖像文化,由於它們通過圖像作用於情感,從而已經並將繼續對表述與價值系統施加的深遠影響。” [lvi]
哈貝馬斯就深刻指出技術理性的泛濫和對人的不斷擴展,造成了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統治”,即“生活世界”的不斷的技術化和體制化。在他看來,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動按一種非工具性原則運作,無須滿足體制對諸如利潤、控制和效率的那些強制性要求。[lvi]看電影、聽收音機、看電視、用電腦或傳真機傳遞資訊、打電話等等都是對交往理性的貶損和踐踏,都是體制對生活世界進行殖民的例證人與人的關係、人的生活越來越幾乎無孔不入地技術化、工具化和規範化,個人的日常生活越來越置於由技術、管理規範、法律等外部強制性的要求、控制和監督中。技術理性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破壞了人際交往正常的、和諧的狀態,個人的自由空間不斷被蠶食,社會-人文生存環境嚴重惡化,生活世界的人文內涵變的日益薄弱[lvi]。可以說,人類由以前的自然人、社會人狀態而變成爲目前的“技術人”狀態。
技術化社會必然是一個風險社會。正由於資訊運動已成爲物質運動、社會運動的基本方式,人類交往的資訊化、網路化和數位化,各類社會主體間和社會事物間及相互之間的關聯性、互動性、開放性和即時性大大增強,人類社會運行狀態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也因此增強。
伴隨科學技術發展而來的動輒就涉及全人類生存安全的各種風險,如從資訊領域、從生物技術、從通訊和軟體領域産生出的新的風險和危險,例如包括金融風險、生態風險、核風險在內的各種可以危及人類、毀滅人類的巨大風險。具體講,當代社會的不確定性來自兩方面,一是社會交往越來越依賴於資訊技術和網路,而由於各種原因隨時可能引起網路安全和資訊安全問題,如黑客的攻擊網路的癱瘓引起經濟政治等各種交往的中斷而導致嚴重的後果;二是由於當代社會的的資訊運動、傳播的技術基礎和機制發生了巨大變化,交往的關聯性互動性整體性的增強,風險的傳遞效應不僅迅速,而且會更加放大。如一個突發事件的資訊傳播速度之快影響之廣在傳統社會條件下是無法想象的,而現在很可能造成社會某子系統以至社會系統的動蕩甚至崩潰。上世紀末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進入新世紀接踵而來的一系列突發危機事件,如“9·11”、“非典”爆發及美國電網系統大癱瘓,其影響之廣、之深,傳播之快,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些足以表明當代社會的高關聯性、高依賴性,傳遞效果的高效率和暫態性,以及極度脆弱性和不穩定性,昭示了當代社會的鮮明特徵。
總之,當今社會是一個交往普遍化和緊密化的“全球化社會”,是一個由資訊化網路化數位化爲構造機制的“技術化社會”,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的“風險社會”,是一個民族國家主權正在在削弱、“世界公共社會空間”日益增長的“跨國社會”,人的存在也正在日益成爲“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歷史的人”,即“世界公民”。所有這些都表明著人類社會形態正在發生深刻的巨變。正如吉登斯所說:“我們正置身於劇烈變動、迷惑無常的時期,興許這表徵著社會形態正面臨著深刻的嬗變。”
二
面對深刻變化的世界,面對方興未艾的全球化趨勢和技術化社會,當代中國哲學的現狀如何?當代中國哲學應有何作爲,應向何處去?這是擺在當代中國哲學研究者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
長期以來,在中國,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倫理學等學科間互不交流、對話,甚至相互輕視,說不客氣點,作爲愛智的哲學卻成爲被肢解和分裂的哲學,哲學家也成爲片面化的、“專業化”的“哲學工作者”。學科體制和學術評價制度以及教學方式的不盡科學合理更強化了這種不正常現象。這樣的哲學顯然無法回應時代的問題,更遑論肩負起指導人們改變世界的使命。
放眼當今世界,的確是一個充滿問題與希望、風險和機遇,喜憂參半的世界。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發生了劇烈而深刻的變化,人類在創造了輝煌的文明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種族衝突、地區戰爭、恐怖主義、熱核威脅、文化矛盾、貧富差距等一系列全球性問題,給21世紀人類生存與發展蒙上了深厚的陰影。生存和發展的困境,實際上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理念的危機,本質上反映了人類文明的危機,也即所謂現代性危機。“資訊時代三部曲”的作者曼紐·卡斯特在其《認同的力量》一書中指出:“當今世界,以及我們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與認同的衝突性趨勢所塑造。資訊技術革命與資本主義的重新構建,已經誘發了社會的新形式——網路社會。這個新的社會組織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擴散至整個世界,一如20世紀工業資本主義及其孿生敵人——工業國家主義,搖撼制度,轉化文化,創造財富和引發貧窮,刺激貪婪、創新以及希望,同時又加諸苦難與灌輸絕望。不管是否美麗,但這確實是一個新世界。”(參見曼紐·卡斯特《認同的力量》序論)
如何處理和解決這些危機,建立公平合理的人類生活秩序,不僅是當今各國思想家和政治家們費心探索的課題,也是關心人類命運的全球公民正在努力的實踐。聲勢浩大的反全球化運動、綠色運動、女權運動,甚至接連不斷的恐怖主義活動和此消彼起的局部戰爭,實際上都是人類危機的直接表現和解決危機的不同方式。而諸如什麽普世倫理、普遍價值、交往理性、跨文化理解和對話、回歸生活世界、生存哲學本體論、正義倫理和以追求差異、邊緣、多元爲學術旨趣,反對中心主義、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的各種後現代思想,則都是哲學回應時代問題和試圖解決危機的思想建構之表現,都是對現代文明危機哲學方式的回應,因而是人類智慧的體現。
哲學是思想中的時代。在反思和批判中提出並建構體現公共理性和人類公共利益指向的哲學理念,是哲學表徵自身存在和實現自身價值的惟一方式。哲學的價值就是爲人類生活、人類社會合理和諧的秩序提供哲學意義上的論證,也即提供表徵人類生存理想的精神家園,以及與之相應的思維方式。因此,如何對當代人類的生存困境,文明的理念和模式進行批判性反思,如何在解答威脅人類文明進步的全球性問題中,實現自己在新世紀的歷史使命,已成爲當今世界哲學研究的重大課題。當今,我們迫切需要研究以下一些問題:
——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堅持和發展問題。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是唯物史觀的重要內容。在當代,由於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和全球化浪潮所導致的生産方式和社會結構的變革,當代社會形態性質、特徵發生了新變化,當代社會的組織結構及運作機制的特點。如何理解這種新變化和新特點,如何評價西方各種社會形態理論(後工業社會論、資訊社會論、知識社會論、全球社會論、消費社會論等)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爭論。如何在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社會形態理論和把握時代特徵的基礎上,形成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複雜現象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解釋框架和理論範式,實現唯物史觀在當代的新發展,無疑是一項具有重大理論意義;不僅如此,通過對社會形態的分析研究,可進一步認識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體系,科學地預測人類社會發展的未來,爲後發國家的跨越式發展提供理論支援;正確認識社會形態的演變及在當代發展的基礎,將有利於我們研究把握社會存在及運動機制的複雜性和新特點,爲科學合理有效解決社會矛盾,推進社會發展,特別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爲使我們的思維方式、實踐方式和決策方式反映社會形態的新發展提供理論基礎的支援。
——馬克思社會生産理論的堅持和發展問題。面對20世紀末以來科學技術革命的新特點,科技社會化、社會科技化已成爲當今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事實和態勢,以知識生産和知識勞動爲重要內容的知識實踐已成爲人類實踐的主導形態。知識實踐是人類實踐發展中新分化出來的重要形態,是科學技術不斷革新發展及廣泛滲透和運用於社會生産和社會生活而形成的結果,它反映了知識成爲人的生存活動方式這一當今的“時代精神”。知識實踐已成爲經濟發展和人類社會進步的基本動力。那麽,究竟如何認識這一實踐形態在人類實踐活動體系中的地位,如何認識這一實踐形態與物質生産、精神生産形態的關係,這實際已涉及到馬克思社會生産理論在當代的堅持和發展問題。
——馬克思文化理論的堅持和發展問題。“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同時,“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3、664頁)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於經濟、政治、文化三者之間關係的基本觀點。面對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和綜合國力劇烈競爭,面對世界範圍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文化在國家綜合國力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文化的交流和傳播越來越成爲各國關係的重要內容,文化的矛盾和衝突也越來越成爲國際競爭和國際衝突的一個方面。當前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是綜合國力之間的競爭,根本的是民族素質和人才之間,實際上是民族文化之間的競爭。那麽,如何從唯物史觀的社會發展動力理論的高度,深刻認識文化在當代和未來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何深刻認識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互相依存、相互促進的辯證關係,無疑是一個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課題。
——關於文化的媒介化、視覺化和審美化轉向對人的生存和社會發展的影響。當代社會文化的一個突出變化是文化的媒介化、視覺化、生活化、經濟化和日常社會生活的審美化,以媒介文化或視覺文化爲主要內容的新文化形態已經産生。由於資訊技術、網路技術和電子媒體的迅猛發展和廣泛運用,人類越來越生活在符號化、影像化的社會環境中,生活在完美的虛擬實在之中。正如費塞斯通、波德裏亞與傑姆遜等後現代主義者指出的,今天生活的環境它越來越像一面“鏡子”,構成現實幻覺化的空間;人類正生活在一個“仿真”的世界,一個由符號包裹的影像世界。正是現代社會中影像的生産能力的逐步增加、影像的密度的擴大,把我們推向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實在與影像之間的差別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審美的方式呈現出來,也即出現了仿真的世界或後現代文化[lvi]。貝爾認爲,“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一種印刷文化”,“印刷不僅強調認識性和象徵性的東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強調了概念思維的必要方式。視覺媒介——我這裏指的使電影和電視——則把它們的速度強加給觀衆。由於強調形象,而又不是強調詞語,引起的不是淨化和理解,而是濫情和憐憫,即很快就被耗盡的感情和一種假冒身臨其境的虛假儀式”。[lvi]吉登斯特別強調印刷媒體和電子媒體的融合,“早期報紙(以及所有種類的其他雜誌和期刊)在把空間從地點中分離出來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由於印刷和電子媒體融合以後,這個過程才成爲一種全球化的現象。”[lvi]
媒介文化、視覺文化正在深刻地改變世界。電視文藝、大衆音像、流行歌曲、綜藝報刊文化和網路多媒體文藝等大衆文藝形式實際上已成爲文化的主導形式。原先的紙質文化形式如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繪畫和以雕塑、音樂、舞蹈等代表的高雅藝術等精英文化,代之以廣告、流行歌曲、時裝、電視連續劇乃至環境設計、城市規劃、居室裝修等視覺文化和直觀文化佔據文化的主導形態。如何正確認識這一文化轉向對人類文化的存在生態和發展趨勢的影響,如何正確認識這一文化轉向對人的存在方式影響,如何在實踐上對待這一文化轉向,後現代主義思想家提出並探討了這一課題,而目前我們還缺乏深入研究。這的確是一項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課題。
——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堅持和拓展問題。在全球化和技術化社會條件下,人類的創造性空前增強,人類的活動範圍和效應大大擴展,這固然是人類本質力量增長的表徵,也凸現了人類空前重大的責任。社會形態的變革,不僅要求人與自然關係有新的理念和規範,也要求人的活動有新的規範。由分歧、衝突到尋求對話和共識,制定共同遵循的規範,成爲維護人類正常、和諧的生活秩序的基本方式。特別是在當今社會,人類面臨許多危及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迫切呼喚著生態倫理、生物倫理、網路倫理、科學技術家的倫理道德以及體現社會公正的政治哲學和人文精神的建構。如何適應時代要求,建立新的道德哲學體系和社會(政治)哲學理論顯然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課題。
其他諸如馬克思的階級階層理論;馬克思的民族國家理論;全球化趨勢和民族文化的發展;全球化和技術化社會條件下的民族發展道路問題,等等,都是需要集中力量進行研究和正確回答的重大課題。
三
全球化和技術化社會,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綜合性問題叢生的時代,是一個需要各種技術專家,更需要思想家,特別需要哲學家,需要大智慧的時代,從而必然是一個跨學科研究大有作爲的時代。這樣的時代給我們的哲學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這就是知識的整合和視界的融合。否則,即使有九天雄心,也無法實現自身的價值。
在這樣一個文明矛盾和危機叢生的時代,我們不禁要感歎,也更深切地體悟到馬克思那句名言的精闢和深刻,即他在那個時代就已指出的,哲學不僅僅要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我們認爲,哲學不僅僅是一種思想理念,更是一種活動。在重視文本研究的同時,哲學必須將其關注的目光投向現實,,以他獨具的高瞻遠矚和深邃洞見的智慧之光影響世界,改變世界,爲人類文明擺脫危機,提供理想世界的指引。因此,我們必須打破學科壁壘和狹隘淺薄的門戶之見,加強論辯和對話。這本來就是哲學和哲學家存在的方式。
因此,面對深刻變化的世界和時代問題,哲學要承擔起指導人們改變世界的責任,首先必須積極倡導和推動哲學各學科間的交流對話,實現方法、視野的互補和相互激蕩,從而實現思想的提升和創造。
一是整合和融彙古今哲學資源和不同流派,促進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與時俱進,建構有中國特色和內涵的中國哲學形態,這在全球化趨勢加劇,西方文化和學術占強勢狀態的背景下尤爲顯得意義重大。
二是通過這樣的推動和整合,無疑可以使中國哲學在解決當代和未來人類生活的重大難題中做出應有和更大的貢獻。中國目前已經完全踏上了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舞臺。世界的發展與中國前途息息相關。中國已經跟西方跟了一百年,不能再做西方思想的奴隸了。我們必須提出合乎本國國情的理念和自己的價值觀。
三是我們不僅要與先哲的思想對話,也要與各種當代西方思潮對話,更要加強我們自身間的對話和交流。我們應多爲這種對話和交流搭建平臺,爲中國哲學、中國學術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爲達至這樣的目的,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爲指導,放眼全球,著眼變化,捕捉問題,聚焦主題,展開有深度的交流、對話和論辯,這才有可能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構起既體現民族特色又反映時代精神的當代中國哲學形態。
[lvi] R·舍普等:《技術帝國》,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4頁。 [lvi] 參見博德裏亞《消費社會》(劉成富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lvi] ]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傳媒》,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40頁。 [lvi] R·舍普等:《技術帝國》,第98頁。 [lvi] 讓·拉特利爾:《科學和技術對文化的挑戰》,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24頁。 [lvi] 參見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65頁)。 [lvi] 參見J·哈貝馬斯、 M·哈勒《作爲未來的過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2頁)。 [lvi] 參見費塞斯通《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譯林出版社,2000年),博德裏亞:《消費社會》(劉成富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瞻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lvi] 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第156-157頁。 [lvi] 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三聯書店,1998年,第27頁 。牟宗三形著說質疑
楊澤波
內容提要:形著說雖然是牟宗三先生儒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有關的系統研究卻較爲罕見。本文意在打破這種狀況,向這一著名觀點提出若干質疑。本文依次從心體是否需要性體保證其客觀性,性體能否保證心體的客觀性,形著說能否達到預期目的,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天道等方面提出自己意見。本文總的結論是,形著說雖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但其路子從一開始就沒有走對,不僅不能有效解決理論上的難題,而且有疊床架屋之嫌。
同自律說一樣,形著說也是牟宗三先生儒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現在學術界討論自律說的文章和專著比比皆是,關於形著說的研究相對而言卻十分罕見。不少學者對此只是一般性地介紹,並不作出自己的價值評判,即使是那些對此明確持不同意見的學者,往往也不亮明具體的理由。[lvi]本文旨在打破這種狀況,提出自己的見解,向牟先生這一著名的觀點提出若干質疑。
一
形著說簡單而言就是以心彰性,以性定心之說。其最顯著的特點,是首先分設心體與性體,其中心體爲主觀性原則,是“形著之主”,性體爲客觀性原則,是“綱紀之主”,心體性體各有其長,各有其用,最後又能合併爲一,結成一體。
首先,心體爲主觀性原則,是“形著之主”。“形著”之說出於《中庸》的“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牟先生借用此說並指出,“心是主觀性原則,形著原則,言性惟因心之覺用而始彰顯形著以得其具體化與真實化。心爲物宰是因其爲性之‘形著之主’,心性合一,而爲物之宰也。”(《心體與性體》,臺灣正中書局1968年版,第二冊,第439頁。以下引用此書不再注明版本)意思是說,只有通過心才能使性發揮作用,才能得其具體性與真實性,所以心是“形著之主”。因此,所謂“形著”就是能夠使性體彰顯其存在,充分發揮其作用的意思。
“形著之主”又叫“心爲性之主”。“於性說流行,是客觀地虛說,亦是形式地說,其落實處是心之自覺之‘形著之用’。無心之形著之用,則性體流行亦只潛隱自存而已耳。心爲性之主,與性爲氣之主,此兩‘主’字意義不同。性爲氣之主是客觀地、形式地爲其綱紀之主,亦是存有論地爲其存在之主;心爲性之主是主觀地、實際地爲其‘形著之主’,心與性非異體也。至乎心體全幅朗現,性體全部明著,性無外,心無外,心性融一,心即是性,則總謂‘心爲氣之主’亦可,此就形著之圓頓義而言也。”(《心體與性體》,第二冊,第438頁)牟先生喜歡說性體流行,但這個流行中真正能夠發揮作用的是心,即所謂“其落實處是心之自覺之‘形著之用’”。當然,達到極致處,心體全幅朗現,性體全部明著,心無外,性無外,心性融一,但作爲初始來說,還必須強調心的作用,只有心活動起來了,性才能真正得以活動,才不至於只是潛存自存。
另一方面,性體爲客觀性原則,是“綱紀之主”。牟先生分心體與性體,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就是強調心是主觀的,性是客觀的,沒有性,心的客觀性就無法得以保證。用他的話說就是:“客觀地順體言之,是融心於性。主觀地形著言之,是融性於心。融心於性,性即是心矣。融性於心,心即是性矣。……融心於性,性即是心,則性不虛懸,有心以實之,性爲具體而真實之性,是則客觀而主觀矣。融性於心,心即是性,則心不偏枯,有性以立之,(挺立之立),心爲實體性的立體之心,是則主觀而客觀矣。分別言之,心是形著之主,性是綱紀之主。”(《心體與性體》,第二冊,第487頁)心和性可能從兩個方向講:從性的方向講,是融心於性,使性不虛懸,因爲有心以實之,這就是前面講的心爲“形著之主”;從心的方向講,是融性於心,使心不偏枯,因爲“有性以立之”,這就是這裏講的性爲“綱紀之主”。所謂“綱紀”就是主持、導節,保證心確有客觀性,不使其走偏方向的意思。
具體而言,以性體保證心體的客觀性是爲了杜絕王門後學的種種流弊。牟先生認爲,在重視心體的基礎上,再談於穆不已之性體,並非錦上添花的簡單重復,實有學理上的必要。因爲心雖貴,但如果沒有性,心也不能保證其客觀性。心體之主觀活動必須步步融於性體之中,才能得其客觀而貞定,即所謂“通過其形著作用而性體內在化主觀化即是心體之超越化與客觀化,即因此而得其客觀之貞定”(《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版,第454頁。以下引用此書不再注明版本)。在牟先生看來,這是堵住王門後學“情識而肆”和“虛玄而蕩”之流弊的根本保證。
總之,心是主觀性原則,是“形著之主”,通過心使性的意義完全彰顯出來;性是客觀性原則,是“綱紀之主”,通過性使心的活動有堅定正確的方向。“形著之主”與“綱紀之主”的作用是不同的。“形著之主”主要是說,雖然性很重要,但真正能夠發揮作用的是心,如果沒有聖人之仁心,根本談不上參贊天地之化育。無論是講天道還是講性體,落實到最後,真正發揮作用的只能是心。應該說這個道理並不難理解,不會有大的爭論。然而,性是“綱紀之主”就不一樣了。牟先生提出這種說法,目的是要以性體保證心體的客觀性,“得其客觀而貞定”,以杜絕王門後學的種種流弊。在我看來,這種說法目的雖好,但至少有如下四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詳加探討。
二
如上所說,牟先生將性體規定爲“綱紀之主”,意在通過性體保證心體的客觀性,使心體的活動有堅定正確的方向。然而,這裏隱含著這樣一個問題:心體爲什麽必須通過性體保證客觀性呢?難道心體自身沒有客觀性嗎?
要弄清這個問題,必須從何爲心體說起。在牟先生的學理中,“‘心’以孟子所言之‘道德的本心’爲標準。”(《心體與性體》,臺灣正中書局1968年版,第一冊,第41頁)也就是說,心體之心是“道德的心”,或“道德的本心”,不是血肉之心,心理學之心,也不是認知之心。大概是因爲道德之心是內在於己的,有強烈的主觀色彩,所以牟先生便將心體規定爲“主觀性原則”。又因爲心體爲主觀性原則,完全聽任於主觀肯定要陷入流弊,牟先生才沿用《中庸》《易傳》到五峰蕺山一路的基本義理,希望能夠以性體保證心體的客觀性。
我認爲,這種思路是大可商量的。在我看來,道德本心既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其本身就有強烈的客觀性,並不需要另外一個性體來保證其客觀性。道德本心是儒家心學的起點,但究竟什麽是道德本心,受到時代條件的限制,歷史上人們並沒有予以明確的回答,沿用古代天論的傳統,稱其是“天之所與我者”,是生而即有的。然而,從理論上分析,道德本心不過是由社會生活和理性思維在內心結晶而成的心理境況和境界,即我所說的倫理心境。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總要受到社會生活的熏習和影響,這種影響久而久之會在心中形成某種結晶體。與此同時,人們也要不斷進行理性思維,理性思維的進行,總會在內心留下一些痕迹,這叫做理性的內化。社會生活和理性內化的結果,在倫理道德領域,就是形成一定的倫理心境,這就是儒家通常所說的道德的本心。[lvi]
從道德本心的來源可以清楚地看出,道德本心是內在於人的,我之好善,我之惡惡,都是我個人的主觀傾向,相對於外界而言,染有明顯的主觀色彩,所以有主觀性的一面。但同時也具有社會的客觀性和普遍性,所以道德本心又有客觀性的一面。比如,孔子論仁,孟子論心,一項重要內容是孝親敬長。孝親敬長當然出自個人的情感,有主觀性,但這種主觀性的根源仍然是客觀的,是客觀的社會生活在內心的生動寫照。要解釋這種情況,可以從鄒人的習俗中找到答案。鄒屬於邾婁文化,可歸於炎族文化,是典型的以倫理爲本位的文化,其民彬彬禮讓,文質相宜,自唐虞以來一直比較發展,遠在其他各地之上。鄒文化最早是從邾婁文化發展而來的,其間雖然經過變革,已經西周化,但邾婁文化重人間親情的傳統並沒有根本消除。在這種地域文化背景下成長的人們毋庸置疑會受其影響。孝親敬長,重視彬彬禮讓的情況見多了,自然會在人們心靈中結晶下來,從而形成一種特有的境況,一種標準。孔子孟子強調愛親敬長,根源全在於鄒人特殊的社會習俗。這種社會習俗在個人內心結晶成爲倫理心境後,人們也就愛親敬長,樂此不疲。這就說明,道德本心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社會生活是客觀的,所以道德本心也有客觀性,並非完全是主觀的。
由上可知,道德本心的形式是主觀的,而其內容卻是客觀的。說形式是主觀的,是因爲道德本心內在於人,而人是主觀的;說內容是客觀的,是因爲道德本心是倫理心境,作爲倫理心境重要起因的社會生活是客觀的(理性思維歸根到底也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社會生活在將自身結晶成爲倫理心境的過程中,也將其客觀性帶進了內心,使道德本心具有了客觀性。因此,道德本心本身就有客觀性,在此基礎上是否還需要再繞一個圈子,通過性體保證其客觀性,是值得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的。
三
上面我們證明了心體自身就有客觀性,並不需要性體保證其客觀性,接下來再來看一看性體能否保證心體客觀性的問題。這顯然是整個形著說的關鍵,需要細細梳理。
在形著說中,性體之所以能夠保證心體的客觀性,是因爲性體來源於天道,天道是性體客觀性最基本的保證。這種客觀性牟先生叫做“道德實踐所以可能之先驗根據(或超越的根據)”(《心體與性體》,第一冊,第8頁)。解決這一問題,根據儒家的思想傳統,一定離不開天道。牟先生認爲,宋明儒以六百年之長期,費如許之言詞,其所宗者不過是《論語》《孟子》《中庸》《易傳》《大學》而已。而這五部經典中,特別重要的又可系於兩詩,即:《大雅·烝民》中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以及《頌·維天之命》中的“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于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通過孔子之言仁,孟子之言本心即性,《中庸》《易傳》即可認性體通於天命實體,並以天命實體說性體也。故此圓滿發展即可系之於此詩,而以此詩表示之也。此兩詩者可謂是儒家智慧開發之最根源的源泉也。”(《心體與性體》,第一冊,第36頁)《烝民》和《維天之命》在《詩經》中的地位原本並不特別突出,牟先生特意將其抽取出來,強調先秦《論語》《孟子》《中庸》《易傳》的義理主脈皆系於此,目的就是要充分肯定天是道德實踐所以可能的先驗根據或客觀根據。
作爲道德實踐所以可能的先驗根據或客觀根據,天道有兩個重要的特徵。其一是“不已”,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的“不已”。其二是“秉彜”,即“民之秉彜,好是懿德”的“秉彜”。天道創生不已,不斷將自己的內容稟賦在人身上,人一旦秉賦到了天道,也就具備了道德的先驗根據和客觀根據。這個過程牟先生叫做“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他說:“‘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即得夫本體宇宙論地說的天命誠體神體以爲吾人之性體,而此性體即心體也。本體性的心體之實並未從性體中脫落也。”(《心體與性體》,臺灣正中書局1969年版,第三冊,第238頁。以下引用此書不再注明版本)“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強調天地之心的內容盡在我心,即“天命誠體神體以爲吾人之性體”。這樣,性體便與天地之心爲一,其客觀性也就得到了保證。牟先生對此有一個很形象的說法,叫做“自然而定然”:“統天地萬物而言曰‘天’,即道體也,即創造的實體也,吾亦名之曰‘創造性之自己’。對個體而言,則曰性體。性體與道體,立名之分際有異,而其內容的意義則一也。說‘性體’,乃自其爲固有而無假於外鑠,爲自然而定然者,而言”(《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490頁)。統天地萬物而言叫做天,天是一創造的實體,又叫道體。道體落於個體之中,即爲性體。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性體其實就是固有而毋需外鑠的意思。道體與性體名稱雖然不同,內容卻是一樣的,都是強調其客觀固有性。說到最後,無論是講“在天”還是講“本天”,都是一個意思,這就是“自然而定然”。
牟先生根據古代天論的傳統,由天說到性,由道體說到性體,通過天道保證性體的客觀性,再由性體保證心體的客觀性,終於使道德的先驗根據和客觀根據有了著落。但是,對於這樣一套說法,我是心存疑慮的。我一直在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將天道作爲性體的來源,真的能夠保證性體並通過性體保證心體的客觀性嗎?換句話說,以天道說明性體的來源和性體的客觀內容究竟是什麽關係呢?經過長期的艱苦思考,我得出了一個與牟先生完全不同的結論:天道並不能通過性體保證心體的客觀性。
我們講客觀性一般有兩個所指:一是存在的客觀性,就是說,它是確確實實存在的,其存在是有理由的;二是內容的客觀性,就是說,它不是主觀臆造的,其內容是有實際基礎的。這兩者不能完全分開,因爲存在往往就是內容的原因,有其存在就有其內容,存在的客觀性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就決定了內容的客觀性。牟先生以天道作爲性體的來源,就是以存在的客觀性說明內容的客觀性。天道是性體的原因,天道是客觀的,所以性體也是客觀的,不僅具有存在的客觀性,而且具有內容的客觀性。但是,應當看到,以存在的客觀性說明內容的客觀性這一方法雖然一般來講是可行的,正確的,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也可能不靈驗,出問題。以天論性,就屬於這種情況。這是因爲,中國哲學確實有以天論性的傳統,但嚴格說來,這種作法只是一種對天的借用,是延續先前的思維慣性,在心理上滿足人形上需要的一種作法。從理論上分析,天不可能是性的真正原因。牟先生以天道作爲性體的先驗根據或客觀根據,以保證性體乃至心體具有內容的客觀性,這一目的事實上是很難達到的。
這涉及到如何理解古代天論傳統的問題,而這又是學界歷來爭論不斷的一個難點,所以不得不多費一些筆墨,簡要回顧一下古代天論發展的歷史過程,爭取從中得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能夠對解決上述問題有所幫助。中國自古就有天論的傳統。在孔子之前,這種傳統大致經歷了不祀非族、有命在天、唯德是輔、疑天怨命四個階段。孔子恰恰生活在疑天怨命階段,懷疑天的思潮對孔子有很大影響。雖然先前以天論德的思想仍然沒有完全消失,但孔子思想的主脈是知生事人,其思想的重點全部放在現實人生之上。孔子全力發明並創建仁且智的心性學說,對天存而不論,使儒學沿著哲學的路子走,沒有發展成神學。中國沒有出現像西方文明中的那種宗教,始終走道德代宗教的路子,根本性的原因就在於此。這是孔子對中國思想發展最主要的一個貢獻。
雖然創立了仁的學說,但孔子並沒有回答人爲什麽有仁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不解決,一種理論學說就還不完整。人類思維天生具有一種“形上嗜好”,總是喜歡刨根問底,直到找出終極的原因方肯罷休。這個特點在儒學發展史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隨著時間的發展,人們不滿足於就仁言仁,而是試圖從人性的角度解決這個問題。《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對性有那麽多論述,說明孔子之後可能爆發過一場關於人性問題的大討論,人性問題當時已經成爲儒學關注的一個熱點。這種情況並不奇怪,說明要想證明孔子仁的學說,必須說明它的來源,而性字原自生字,人們希望從人性上尋找仁的根據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孟子也屬於這種情況。孟子體悟到了自己的道德本心,納仁入心,爲儒學作出自己的貢獻,但與此同時他也必須回答道德本心最終來自何處的問題。依據當時的思維水平,對道德本心的形上根據進行解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面對這種困難,孟子又一次借用古代天論的傳統,指出道德本心的形上根據全在於天,是“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上》第15章)。這些論述都可以說明,孟子的確有意爲性善尋找一個終極原因,最後將這個原因歸結到了天,將天作爲性善的形上根據。
思想史發展的這個內在邏輯要求,也影響到《中庸》和《易傳》。《中庸》開篇就是一句“天命之謂性”,這已經是非常正式地以上天作爲道德的終極根據了。《易傳》又進了一步,明確講“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強調在乾道的變化過程中,萬物各正其性命,直接強調性命之正來於乾道,更加明確了以天論性善的思路。
由此我們不難明白,儒家將道德的根據推給上天,是受到了古代天論傳統影響的結果,先秦儒學以天論德其實不過是一種“借天爲說”的作法而已。所謂“借天爲說”是指對一個問題無法確切回答的時候,將天作爲其終極根據的一種作法。“借天爲說”最大的特點在於一個“借”字,以天作爲事物的終極根據,只是一種借用。換句話說,儒家在這方面講天,是延續古代天論的思想傳統,將道德的終極根據上推到天,從而滿足人們思維的“形上嗜好”罷了。天並不是道德終極根據的真正源泉。
有人可能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爲這樣解釋上天,等於把古代的天論傳統一筆抹殺了,果真如此的話,儒學兩千年發展的形上智慧還有什麽意義呢?我認爲,如此解釋古代的天論傳統只是依據歷史發展的規律還其本來的面目而已,而不是完全否定其歷史的價值。對歷史上的事物進行如實的評價與否定其歷史價值,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如何看待道德理論的形上根據,就屬於這種情況。任何一種道德學說,都必須對其形上根據有一個交待。這個形上根據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信仰的。在西方,這個形上根據或者是柏拉圖的理念論,或者是亞裏士多德的目的論,或者是中世紀的上帝,儘管形式不同,但其終極的地位卻是一樣的。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儒家思想中的這個形上根據只有一個,這就是上天。將天確定爲道德的形上根據之後,儒家的道德學說也就完滿了,沒有缺陷了。你要問人爲什麽要有道德,人爲什麽會有良心,儒學家會告訴你,這些都是上天決定的,是天之所與我者。到這裏,問題已經到底了,不能再問了,這樣至少從表面上看,問題已經解決了。儘管這種解決方式並不圓滿,但它至少從心理上滿足了人們的形上要求。
這方面的情況可以看一看康得。康得在西方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劃定了認識的界限,人只能認識有感性直覺的物件,沒有感性直覺的物件是在人的認識領域之外的。康得的這一學說使西方傳統的形上學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爲康得有力地證明了上帝、靈魂、自由等只是一種假設,人類對此沒有感性直覺,不能成爲理性認識的物件。雖然上帝不是理性認識的物件,但在實踐理性中卻是不可缺少的,因爲沒有上帝這種因素,道德便是不圓滿的。所以康得在實踐理性中仍然保留了上帝,爲其留下了一席之地。康得的這種作法,與他所提倡的道德自律學說,其實並沒有構成原則的衝突。道德必須出於理性的要求,自我立法,自我服從,其中不能存在任何其他的目的。上帝的保留完全是一種潛在的因素,或者說是一種暗含的前提。康得的這種作法對我們有很大啓發,它告訴我們,一種道德理論必須有一種心理的、情感的、目的的要求,以此作爲這一理論的最初動因。過去人們往往認爲,保留上帝是康得學說的不徹底性,批評康得將前門趕出去的上帝,又從後門放了進來。但近來不少研究改變了這種看法。他們看到,一種道德理論必須有一個目的論作爲支撐,否則就是不完整的。18世紀的道德是以神、自由爲內容的目的論體系爲前提條件,所以才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如果沒有上帝等因素的存在,當時的道德能否健康發展,還是一個不小的疑問。
儒學中的天與康得學說中的上帝有幾分相似。單從現象上看,儒學中的天與康得學說中的上帝,都不是其理論中所必需的。儒學論道德,根據或在心,或在理,但不管是心還是理,天都沒有存身之地。康得論道德,根據全在理性,理性自我立法,自我服從,其間也沒有上帝什麽事。但從本質上說,儒學中的天與康得學說中的上帝,又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爲儒學如果離開了天,人們會思考人行善的終極根據在哪里,康得學說不講上帝,人們會詢問我爲什麽應該過善的生活的問題。由此看來,在一個道德學說中保留一個形上的根據,是多麽的必要。儒學中的天所發揮的就是這個作用。我爲什麽要行善,爲什麽要做好人,良心本心究竟來自哪里,這一切的一切,答案都在於天。天是一切善的源頭,最終的根據。這個看起來並沒有特別意義的上天,對於儒者來說,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爲中國古代天論的傳統源遠流長,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對於天是不懷疑的。將道德何以可能的根據置於上天,人們便真的相信,這就是道德的終極原因,不再對這個問題有任何疑問了。這個在理論上看似非常複雜的問題,在儒學史上卻以一種相對比較簡單的“借天爲說”的方式得到了解決。這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可以說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形上之謎”。
既然儒學以天論德只是“借天爲說”,那麽天就不是性的真正的根源。我們可以通過上天讓人們相信善性是“我固有之”的,是“自然而定然”的,但這種作法並不能真正從內容上保證性體並通過性體保證心體的客觀性。前面講過,客觀性可以分爲兩種,一是存在的客觀性,二是內容的客觀性,一般而言,存在的客觀性可以說明內容的客觀性,但這樣做必須有個前提,這就是這個存在的客觀性必須是真實的,否則,以存在的客觀性是不能說明內容的客觀性的。中國古代以天論性就屬於這種情況。哲學發展到了今天,從理論上分析,天不可能是性的真正原因,也不會有人真的相信道德的根據是上天賦予的,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溝通了。既然天不是性的真正原因,當然也無法保證性體的客觀性,這樣一來,我們證明性體無法保證心體客觀性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四
任何理論都有自己的目的,衡量一種理論是否取得了成功,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看其是否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牟先生創立形著說,目的是借助天道性體保證心體的客觀性,杜絕王門後學流弊。但在我看來,這個美好的目的實際上是很難達到的。
爲此,我們不妨主要以蕺山爲例作一些具體分析。明代末期,王學發展爲重重流弊所困,倡狂者參之以情識,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蕺山之時情識之風更是風行一時。顔山農性情怪異,常常做出一些不合常理的舉動,據人記載,一次他在講會之中,忽然立起,就地打滾,如毛驢一般,口中念念有詞:“試看吾良知!”這個典型的事例清楚地說明,當時王門後學確實陷入了放縱之弊。蕺山之學正是爲了對治這種王學流弊而存在的。蕺山認爲,良知心用不加限制必然歸於放縱,於是希望通過區分心宗和性宗的辦法,用性宗對心宗加以一定的制約。梁啓超對蕺山之學的客觀作用有過一個較爲客觀的評價,他說:“王學在萬曆、天啓間,幾已與禪宗打成一片。東林領袖顧涇陽(憲成)、高景逸(攀龍)提倡格物,以救空談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劉蕺山(宗周)晚出,提倡慎獨,以救放縱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際,王門下唯蕺山一派獨盛,學風已趨健實。”(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頁)這就是說,明清之際,經過蕺山的努力,王門流弊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救治。學術界一般均認可梁啓超的這個看法,說明蕺山之學對於救治心學放縱之弊確實有一定的效果。牟先生十分看重蕺山,正是因爲蕺山不滿意于心宗,另立一個性宗對其加以限制。
但是,像蕺山這樣希望通過性宗克服心宗之弊的作法,能否取得實際的效果,本身仍是有待討論的。如上所說,以天論性只是對於古代以天論德思想傳統的一種借用。性只是心的形上根源,天只是性的假借根據,無論是天道還是性體都不是客觀性的全權代表。王學陷入流弊並不是因爲他們不重性體,不講天道,而是因爲他們並不瞭解什麽是真正的良知,所以也就無法真正彌補和糾正良知的不足。道德本心是內在的,對它的認識完全在於直覺,體悟起來並不容易,而當時王學強盛,成爲時尚,一些並不真正懂得心學的人也來不懂裝懂,附庸風雅,參之以情識,夾之於雜念。山農的舉止就屬此類。此類舉動斷然不是真的出於心體,對道德本心有真正體會的人,是不可能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來的。要想從根本上杜絕此類問題,必須明確什麽是真正的道德本心,道德本心來自於何處,而不在於大講什麽天道性體。大講天道性體不能爲心體增加絲毫的客觀性成份。所以,從理論上講,希望以天道性體賦予心體客觀性,從而堵住心學流弊的願望,並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另外,蕺山爲了杜絕王學流弊做的工作是一個整體,區分心宗性宗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其他還包括提倡慎獨,區別意念等等。蕺山提出的“意根最微”之說將意提至超越層,上升爲心之存主,既知善知惡,又好善惡惡,屬於“蘊於心,淵然有定向者”,從而與作爲已發、屬於感性層的念區別開來,爲念把定方向,首次讓人們意識到良知心用不是絕對的,必須用意爲其把關,加以限定。正是因爲如此,蕺山的作法才對當時一任良知心用的放縱之風直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還應該看到,學風的扭轉與當時政治局勢也有一定的關係。明清之際社會政治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話語中心已轉至救亡圖存,抵禦外族方面,在這種背景下,明代末期王學流弊自然所以收斂,有關的種種爭論,已不再那麽重要。如果將這些因素都考慮進來的話,蕺山之學使學風趨於健實中有多少是靠區分性宗心宗而取得的,就值得認真重新思考了。
但是,牟先生並沒有這樣考慮問題,而是沿著蕺山的思路,仍然希望借助天道性體保證心體客觀性的辦法來杜絕心學流弊。牟先生這種作法是否能夠取得實際效果的,是很值得懷疑的。我們不妨來分析一個實際的事例。蕺山在《過惡說》和《證學雜解》中討論了過惡的問題。牟先生對此很重視,認爲人之所以有過惡,是因爲受到了感性的影響,行爲離開“真體之天”(《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第537頁)的結果。人的行動能體現“真體之天”,就沒有過惡,不能體現“真體之天”,就有過惡。因此,要去除過惡,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突出彰顯“真體之天”。這裏的“真體之天”,即相當於天道性體。牟先生如此突出“真體之天”,就是因爲天道性體是道德的唯一來源,強調天道性體,就是突出人的道德意識,突出了道德意識,也就可以遠避過惡之妄了。問題在於,大講“真體之天”就能保證心體的客觀性,從而克服過惡之妄了嗎?在這個問題上,我與牟先生的看法有著原則的區別,這種區別集中到一點即在於:牟先生認爲由《中庸》《易傳》而來的一系體現了天道和性體,是客觀性的代表,以它作保證,心體的客觀性就有了著落,不至於放縱而無收煞;而我認爲,《中庸》《易傳》只是順著人們思維的內在規律,爲良心本心尋找終極的根源,所以天道性體並不是客觀性的代表,並不能真正賦予心體以客觀性,也不能因此而杜絕心學的種種流弊。因此,在我看來,另立一個獨立的性體,大講天道,是無助於克服過惡之妄的。如果一個人不能對自己的道德本心有真切的體會,聽任感性層面而行,或者以假良知充任真良知,參之以情識,發之於顛狂,你對他再講一千遍一萬遍“真體之天”,又有何用呢?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從理論上說明道德本心究竟爲何物,其起源在何方,而不能只是沿用古人的思路,空講天道性體。果真如此的話,人們自然就會明白,每個人都有良心本心,遇事聽命於它,就能成就善行,同時也會知曉,那些就地打滾一類的怪異行爲,放縱之舉絕不是真的良知。當然,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時代條件必須成熟。如果說蕺山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希望以分立心宗性宗的方法杜絕王學流弊是可以理解並充分肯定的話,那麽我們今天再沿用蕺山的老路子就說不過去了。正是在這一點是,我對牟先生的作法一直感到難以理解,不明白爲什麽時至二十世紀下半葉他仍然沿用如此陳舊的思想方式解決如此重要的理論問題。
五
分立性體心體,大講天道,不僅不能達到預期目的,而且還滋生了一些新的理論問題。受本文篇幅所限,這裏只談兩個問題。
首先,天道究竟是什麽?關於這個問題,牟先生有明確的解說:天道是一個能夠起宇宙生化的“形而上的創造實體”(《心體與性體》,第二冊,第23頁)在牟先生學理中,天、天理、天道、道體說法雖有異,意義卻相同,都是指最高的創生實體,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創生覺潤的實體。牟先生這樣講,一個重要目的是爲了說明性的起源,故他有虛說和實說之分:“說帝、天、天道、天命,皆是虛籠之總說,皆是總說之形式字。”“說理,說神,則是進一步克實說,而明其實蘊。說性、尤克實。蓋言帝、天、天道、天命,目的皆在建立性體也,前章所謂皆結穴於性也。”(《心體與性體》,第二冊,23頁)很明顯,牟先生的意思是說,無論是講天、還是講天道,都是一種形式的說法,是一種虛說,真正的意圖是在建立性體,所以只有說性才是實說。
即使如此,我認爲,牟先生將天道視爲一個“形而上的創生實體”的作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爲牟先生的這種作法勢必引出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這個作爲天道的“形而上的創生實體”與其所創生的萬物在時間上是什麽關係?也就是說,它是先於物還是後於物或是與物同時存在呢?如果說天道是一個“形而上的創生實體”,以理推論,它必然是在物之先,否則它無法創生萬物。果真如此的話,問題就嚴重了。
理氣、道器的關係,一直是宋明儒學討論的熱點,討論的焦點之一就在孰先孰後。伊川尚不曾明言理在氣先。朱子由於比較關注宇宙發生的具體過程,所以明確主張理在氣先。這種觀點在當時影響很大,但後來也受到人們的批評,其中也包括劉蕺山。蕺山明確反對朱子理先氣後的觀點,斥此爲異端,認爲“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劉子全書》卷十一《學言》中)蕺山對天的看法也是一樣,認爲天是萬物之總名,並不是統馭創生萬物之君主;道是萬物之總名,而不是淩駕於萬物之上的本體。道德的根據在心,心的根據在性,性是原本固有的,但爲了強調這一點,所以稱其爲天命。天就是理,其生生不已即是命。“別以爲有蒼蒼之天,諄諄之命者,非也。”(《劉子全書》卷八《中庸首章說》)蕺山並非將天視爲高高在上的一個實體,而是強調離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天非與物爲君。蕺山的這一思想反映了宋明兩代理氣思想的進步,常爲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人所肯定和稱道。但奇怪的是,牟先生的形著說雖然以蕺山爲典範,但並不接受蕺山的這一可貴的思想,反而從蕺山後退一步,將天道視爲形而上之實體,個中原因令人費解不已。
其次,天道創生性體是有意的嗎?這裏,我們首先應當肯定,牟先生並不認爲這個過程是有意的,也不認爲天道是一個人格神。牟先生認爲,上世言帝、言天,乃至言天道、言天命,都是關聯著王者受命說的,還有原始宗教的情懷,隱約有人格神之意,至少是承認冥冥之中有一真正的主宰。但自孔子創立仁學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內而言,人們認識到道德的根據完全在於自己的仁,從此將眼光投射到自己身上;對外而言,將原始宗教之天轉化爲天命流行之體,彰著爲化育之德,擺脫了宗教之天的虛歉狀態,使其演化爲一個道德創生實體。經過這個轉化,先秦後期儒家談天,已經沒有了人格神的意思。既然上天不再是一個人格神,那麽其所創生性體就只能是一個自然的無意識的過程。關於這一點,牟先生其實有過明確的說明,他講:“‘生生之謂易’一語,若通體達用地解之,當該是如此,即:能使萬物生而又生、而不止於一生者即叫做是易。此即‘上天之載’之自體也,亦即‘天之所以爲道也’,此亦是天道之自體。‘天只是以生爲道’,此‘生’顯然不指‘易相’言,是指‘易體’言,指生之真幾、能創生之道言。此能創生的道即曰生道,亦曰‘生理’,即能去創生萬物(生物不測)的那‘真幾’(爲物不貳)(此處下引號原文缺失,引者根據文意所補—-引者注),那超越的、動態的、最高最後而極至的原理(根源)也。”(《心體與性體》,第二冊,第137頁)“生生之謂易”是儒學解釋萬物生存原因的一個老傳統,“生生之謂易”,即是生而又生,不止於一個生的意思。以此解釋性體,性體的産生當然也是在天道生生不已的過程中産生的,是一個無意識的、自然的過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雖然不承認天道是一人格神,但又反復將天道與心義聯繫在一起,大講“天地之心”。他說:“問題是在:就此超越的實體說,此實體(道、天道、天命流行之體)究竟還有‘心’之義否?此‘心’之義是實說的實體性的心,非虛說的虛位字之心。當朱子說‘天地之心’,以及說‘人物之生又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時,此心字是實說。但在天地處,此實說之心卻又爲其分解的思考弄成虛脫了。無心是化之自然義,有心是理之定然義。心融解于化之自然義,固已無心之義,即融解于理之定然義之‘有心’,心被吞沒於理,心成虛脫,亦無心義。”(《心體與性體》,第三冊,第260頁)這就是說,道體是一創生實體,要保證其創生性,實體中必須有心的地位,即所謂有心義。這個心又叫“天地之心”。在牟先生看來,“天地之心”即是天地生物之心,即是天命流行之體,其真實的含義是說道體不只是理,而同時也有活動性,有創生性。朱子雖然也講天地之心,但心被吞沒於理,心成虛脫,並無心義,所以朱子講“天地之心”只成分解的思考,並無創生性。由此我們可以明白,牟先生講天必須有心義,講“天地之心”,並不是主張真有一個心在天上,而是強調天要有活動性,有心才能有活動性,無心必然無活動性。
牟先生上述說法是很容易造成混淆的。因爲心是有意志的,大講“天地之心”,很容易使人想到天道創生性體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牟先生否定天是人格神,但又大講“天地之心”,用意究竟何在呢?在反復推敲牟先生有關論述之後,我發現,牟先生這樣做主要是爲闡述其存有論服務的。牟先生認爲,先秦儒學由《論語》《孟子》到《中庸》《易傳》,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直到發展爲一個完整的“道德的形上學”。他說:“先秦儒家如此相承相呼應,而至此最後之圓滿,宋明儒即就此圓滿亦存在地呼應之,而直下通而一之也:仁與天爲一,心性與天爲一,性體與道體爲一,最終由道體說性體,道體性體仍是一。若必將《中庸》《易傳》抹而去之,視爲歧途,則宋明儒必將去其一大半,只剩下一陸王,而先秦儒家亦必只剩下一《論》《孟》,後來之呼應發展皆非是,而孔孟之‘天’亦必抹而去之,只成一氣命矣。孔孟之生命智慧之方向不如此枯萎孤寒也。是故儒家之道德哲學必承認其函有一‘道德的形上學’,始能將‘天’收進內,始能充其智慧方向之極而至圓滿。”(《心體與性體》,第一冊,第35-36頁)這就是說,《論語》《孟子》雖然以主觀面爲主,但也有一個客觀的、超越的天,順此發展,必然達至《中庸》《易傳》,歸於最後之圓成。這叫做“道德意識充其極”,也就是牟先生一貫講的道德哲學必函一道德的形上學。所以,必須既講《論語》《孟子》,又講《中庸》《易傳》,才能將天收進來,才能將儒家道德智慧充其極,才能做成道德的形上學。牟先生一再強調《論語》《孟子》《中庸》《易傳》通而一之,並且非常重視《中庸》和《易傳》,意義就在這裏。
這樣,我們可以大致明瞭牟先生既不承認天道是一人格神,又大講“天地之心”的真正用意。牟先生在寫作《心體與性體》的時候,其道德存有論的學說已經初具雛形。爲了保證這一學說能夠成立,牟先生必須證明道德之心是如何創生存有的。在這個過程中,他分析了古代天論的傳統,一方面借鑒《中庸》《易傳》的思想,以天作爲萬事萬物的總根源,另一方面又直接將心上提到了天的高度,將聖人之心看作天地之心。上天創生萬物,就是天地之心創生萬物,天地之心與聖人之心同,所以上天創生萬物就是聖人之心創生萬物,也就是道德之心創生存有。牟先生的這個思想意圖是非常幽深的,但具體的作法卻不無問題。因爲不管是天地之心,還是聖人之心,心總是有意識的,講上天創生萬物即是聖人之心創生萬物,使人容易想到天道創生性體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從而造成混淆。應當看到,上天創生萬物與道德之心創生存有,是不同的兩個概念,分屬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前者是指萬物之自然,後者則指萬物之存有。如果要證明道德之心能夠創生存有,完全可以直接加以證明,沒有必要借用《中庸》《易傳》中的天的思想,將道德之心與天地之心聯繫在一起,否則必然引發混亂。
總的看來,雖然牟先生關於天道是“形而上的創生實體”的說法並不是講天道是一個人格神,而主要是爲其道德存有論打基礎,實際上,天道創生性體也只能是一個自然的生生不已的過程,但是,他將天道視爲“形而上的創生實體”這種說法本身就存在諸多問題,是一種倒退,必然造成理論上的不缺陷,引發一系列的混亂,讓人誤以爲天道創生性體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學術界對此爭論很多,混淆叢生,這種情況不能完全抱怨他人理解力不夠,牟先生自己表述方式不恰當不清晰也是不可否認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
最後,將我對形著說的看法做一個簡要的總結。
形著說主要是沿用五峰蕺山的思路,爲杜絕王學流弊而創立的。陽明之後,心學的發展漸漸走向極端,蹈空放縱之弊日盛。有責任感的哲學家自然要以解決這一問題,使心學發展走上正軌爲己任。蕺山如此,牟先生也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牟先生是“接著”蕺山講的。所以,牟先生創立形著說與其說是挑明五峰蕺山的學脈特點,變兩系爲三系,不如看作是牟先生自己思想的一種理想形態,是牟先生爲解決儒學發展過程中的這一重大問題而提出的一種方案。爲了達到這一目的,牟先生充分吸收蕺山之說,先講一個性體,再講一個心體,然後講心體有形著的能力,通過形著,得其客觀性,從而使道德理論既有主觀性,又有客觀性,完整而圓滿。這種理論看似完整,方方面面都講到了,但其中也隱含著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其中主要包括:爲什麽必須用性體保證心體的客觀性,心體難道本身沒有客觀性嗎?以天道性體作保證,真的能使心體具有客觀性,從而杜絕心學流弊嗎?天道是如何創生性體的,天道難道真的是一個形上創生實體嗎?
形著說之所以存在這些問題,主要是因爲牟先生對作爲道德根據的心與性缺乏一個合理的解釋。從有關的論述看,牟先生對道德本心的體會是非常深刻的,但他對道德本心並沒有一個具體的理論說明,不瞭解道德本心的真正起源。當他看到陽明後學陷入重重流弊,蕺山分立心宗性宗以克服這些流弊的時候,似乎受到了啓發,感受到性體的重要,便沿用五峰蕺山的思路,大講天道性體。雖然這種方法也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平心而論,這條路子一開始就沒有走對。從理論上說,作爲心體的道德本心不過是社會生活和理性思維在內心結晶而成的倫理心境。古人由於不瞭解這個道理,又要對道德本心的形上根據有個交待,才借用源遠流長的天論的傳統,將道德本心的根源追溯給了上天。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古人的這種作法中,上天只是道德本心的一個假借的根源,不可能從理論上真正說明道德本心的來源。所以借助天道性體不可能真的賦予心體以客觀性,解決心學的種種不足。因此沿用“天命之謂性”的思路,將心體的客觀性寄託在天道性體上,以此來解決心學後期發展中的種種問題,是不可能取得理想的實際效果的。歷史上蕺山歸顯於密,分立心宗性宗,雖然有扭轉學風之功,但不可能從根子上解決問題。時至今日,牟先生“接著”蕺山講,仍然希望用天道性體保證心體的客觀性,從理論上說也不可能真正達到預期目的。
形著說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而且由於分立心體與性體,使其理論形式過於複雜纏繞。心體與性體的特點各不相同,如果將二者分立開來,自然要對二者的不同特點有所規定,於是就有了內在與超越的對立,內在體證與超越體證的對立,自覺與超自覺的對立,對其自己與在其自己的對立:心體是內在的,性體是超越的;對本心的直覺是內在的體證,對超越之體的直覺是超越的體證;心體是自覺,性體是超自覺;心體是對其自己,性體是在其自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不同的說法不要說一般讀者,即使是專業人員,不花費極大精力也是難以掌握的。人們常常抱怨牟先生著作難懂,曲曲折折,與此不無關係。
其所以出現這些問題和麻煩,完全是由分設心體性體造成的。思想家由於個人的特質不同,考慮問題角度不同,其理論傾向總有自身的特點,有的重心,有的重理,有的重性,我們應當承認這些差異。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不同特點的學說能否有效地解決當時的理論問題,如果能夠解決,我們就應當接受,不管其理論形式如何,否則,我們就很難接受。分設心體性體不僅沒有在理論上成功解決心學流弊的問題,而且還在理論上造成了新的衆多麻煩。道德的根據完全在於心,性不過是心的出處和根源,這就是心性原本爲一而不爲二的最深層的原因。質言之,只有一個心體,沒有另外一個獨立的性體。牟先生那種先以《論語》《孟子》爲主,再繞到《中庸》《易傳》,從而保證其客觀性的辦法,從一開始就找錯了方向,走錯了路子。心學後期産生的種種問題可以通過其他方法,而不需要用分立心體與性體的辦法來解決,否則必然造成重復纏繞,使原本簡單明瞭的儒學變得異常曲折複雜,晦澀難解。這種情況用象山的話來批評,就是疊床架屋。平心而論,形著說所能解決的問題,並不比其造成的麻煩更多。所以,我不贊成形著說,也不認爲將五峰蕺山獨立爲一系有特別重要的理論意義,儘管我承認形著說的願望是好的,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非常迫切的。
[lvi] 有關情況可參見鄭家棟《斷裂中的傳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81-182頁。 [lvi] 將道德本心解釋爲倫理心境是我多年來讀解儒學的一個核心觀點,具體請參閱拙著《孟子性善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孟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的基本理論特質及其後現代意義
李翔海
內容提要: 近年來,與全球範圍內對環境與生態危機的深入反省密切相關,中國哲學的“生態意蘊”成爲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本文擬對中國哲學所蘊涵的“文化生態模式”的基本理論特質予以探討,並進而申論其“後現代意義”。這裏所謂“文化生態”,是指由構成文化系統的諸內、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態關係。“文化生態模式”則是指維護文化生態生存、綿延的根本律則與運行機理。而之所以探討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的“後現代意義”,主要是爲了更有理論針對性地突顯其對尋求“現代之後”人類文化更爲康健的存在形態所可能有的借鑒意義。
一
文化是人類精神的外化。由於人是以類的方式存在於大宇長宙之中且具有超越祈向的社會動物,一個文化系統的文化生態必然涉及到人與終極實在、人與自然宇宙、個人與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間的關係。正是這些方面構成了特定文化系統的基本存在形態,亦即其文化生態模式的基本“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爲“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概要而言,它包括了以下兩方面的基本理論特質。
第一,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爲緊密相連的一體。正如不少論者已指出的,中國哲學看待天地宇宙以及萬物的基本範式就是“生命典範”的,即自覺地把天地宇宙以及萬物均看作是類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這在作爲中國哲學之思想源頭的《周易》哲學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周易》借助於卦爻符號,建構了一個縱貫天、地、人,橫闊時、空與變化而又一體相連的整體宇宙系統。貫通這個系統的基本範式正是生命典範。《周易》不僅肯定了天地宇宙、萬事萬物是處於永恒變化、運動過程中的,而且鮮明地將“易”解釋爲生命的流行。《系辭》“生生之謂易”的界定就明確地說明,變易的本質特徵正是生命的大化流行。在此基礎上,《周易》不僅把天地看作是包括人類在內的萬物生命的根源(《說卦傳》:“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而且明確地把天地最高的德性看作是“生”(《系辭》:天地之大德曰生)即不斷地創發新的生命與生機、生意,這就進一步從“生命典範”的視角揭示了天地宇宙、萬事萬物之間作爲“生命”一體相聯的內在關聯。正是借助於生命典範,《周易》建構起了一個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萬物”、“範圍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貫之的機體網路系統。《系辭》明確指出,“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道是至易簡而又至廣大的:“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沿著《周易》哲學所開闢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爲主體的中國哲學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一以生命典範貫通天地萬物的世界圖式。儒道雖然在某些理論關節點上有著相當的差異,但在基本的“世界觀”上又堪稱共同繼承了《周易》哲學的基本精神,從而形成了“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論”。在這一世界圖式中,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既各自構成了相對獨立的系統,又共同構成了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它們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種內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構成了萬物的存在根源,同時也是貫通萬物的內在本性。以生命體存在的萬物統領於“道”或“天道”,共同構成了充滿生機的大化流行。由於大宇長宙的大化流行、生生不已被看作是一個自然而然、沒有主宰亦不需主宰的永恒過程,因而這個世界圖式中就不可能給類似西方的作爲天地萬物創造者的上帝留下存身之地,在成熟形態的中國哲學中就不可能保有人格神的地位。由此,被看作生命之終極根源的“天”或“道”得以取代西方文化中上帝的位置,成爲終極關懷所依託的“終極實在”。
其二,作爲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人文主義是中國哲學傳統的一個重要特色。而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與西方現代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又有著“內在的人文主義”與“外在的人文主義”之別⑴。
中國哲學“內在的人文主義”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從“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的世界圖式出發,突顯了人與天地萬物的內在關聯。它強調,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人是內在於而非外在於天地萬物的。《周易》哲學從兩方面突顯了天地萬物對人的內在性。其一,天地萬物構成了人之所以爲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確指出:“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這顯然是把天地萬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說卦》指出:“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叠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這也清楚地說明,天地人及其運行律則是融爲一體的,人在存在形態上是不外於天地宇宙的。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價值之源,人之所以爲人所應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結果。《乾·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的論斷,直接揭示了作爲天之表徵的乾道與萬物之本性的關係:正是天道的變化爲萬物本性的貞定確立了根據。這也就爲人在德性上效法天地提供了可能。由此,《易傳》進而明確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泰·象辭》)指認爲是人的責任與義務。這樣,《周易》事實上是將天地之德看作人之德性的形上根據。這從《系辭》“生生之謂易”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論斷中即可清楚地見出:“生”不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態,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爲人類提供了價值的源頭。由此,《周易》開啓了後儒以“生”釋“仁”,將人之本質屬性與天地之德相聯繫,以爲之確立形上根據的基本精神方向。
與此同時,人作爲大宇長宙中唯一具有靈明者,又不是完全類同於其他萬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種特殊使命,即通過人的存在而不僅更爲充分地實現天地之道,而且使之發揚光大。《論語》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所謂“盡心知性以知天”、所謂“踐形”,《中庸》所謂“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言明的就是這個道理。張載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堪稱是十分典型地代表了中國哲學對於人之使命的基本體認:人之所以爲人的存在之理要求,人不僅要通過效法天地而成就自己作爲人的德性,而且還有著內在的義務與責任將其德性施之於天地萬物,以切實盡到參贊化育之責,充分地實現天地生生之德,使大宇長宙更加充滿生機與活力。在這裏,張載不僅鮮明地展示了天下一家、民胞物與的仁者氣象,而且道出了一個挺立於大宇長宙之間的仁人志士的“天地情懷”。當然,在中國哲學中,人雖有著與其他萬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這一特殊使命歸根結底依然是爲了實現天地萬物自身本有的內在價值,其特殊之處只在於:只有通過作爲天地之靈明的人的努力,天地萬物自身本有的價值才能實現得更爲充分亦更爲豁顯。
二
立足于“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的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表現出了頗爲獨異的理論特質。與本文的論旨相關聯,接下來將主要對其中的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等三方面加以具體的梳理與分析。
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的一個頗爲顯明的理論特質是對普遍和諧的追求。正如成中英先生指出的,追求和諧化是中國哲學中包括《周易》哲學、儒家哲學與道家哲學共同具有的價值取向⑵。即以儒家而言,對普遍和諧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他不僅明確標舉了對日後整個中國哲學均産生了深刻影響的“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的旗幟,而且以自己的躬行踐履向世人展示了一個力圖在人與天地宇宙、個人與他人、個人之身心、人世間與幽冥界之間追求普遍和諧的生命存在形態⑶。《中庸》指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這是將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礎上的普遍和諧看作是天地之道的題中應有之義。在另一處,《中庸》將此意表達得更爲明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明確地表示,建立在“中”這一天下之大本基礎上的“和”是天下之達道,人能夠達致天下之達道,則可以使天地萬物達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原始儒家揭明的追求普遍和諧的理論意向經後儒的不斷發明推擴而成爲儒家基本的價值取向之一。這從朱熹對上引《中庸》一段話的解釋中就不難窺出端倪:“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這是說,通過人的踐性成德以致中和,其極致即可達到“天地位”而“萬物育”的理想境界。
正如朱熹將“和”與“生”相聯繫所顯示的,在儒家哲學中“和諧”與“生生”是緊密相連的。“仁”既是人之爲人的本質所在,又是維護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規範,而天地也以其不斷創發、培護出新的生機與活力而表現出仁的最高形態—-生生之德。由此,不僅人世間是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而且上達于天宇、橫闊於萬物,也無一不被大化流行的生生之意所充滿。立足於仁之通內外、貫天人、徹幽明的感通遍潤的發用,儒家追求一種人之自我身心、個人與他人、人與自然、人與超越之天地宇宙的普遍和諧。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大宇長宙不是趨向於事物之間由於差異而生産矛盾和不協,而是趨向于事物之間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礎上的相互依賴、相互成就的“太和”狀態。人作爲天地間唯一具有主觀能動性因而最爲珍貴的存在者,其重要的存在使命就是促成和諧、消除不和諧狀態,以充分體現天道之“仁”。與此同時,“生生”與“和諧”又是貫通爲一的。一方面,離開了具有差異性之事物的相互補充、相互調節,大宇長宙就只能是死水一潭,難以煥發出生機與活力。另一方面,也正是由於大宇長宙之生命本身就表現爲大化流行,處於差異甚至矛盾之中的事事物物才可能在不斷變化與演進之中趨於和諧。“生生”與“和諧”的一體,共同構成了儒家人文主義的基本價值系統。擴而大之,亦可以說,“生生”與“和諧”的一體,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想。由此,對包括人、人類社會與自然宇宙在內的萬事萬物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太和”之境的追求,就成爲中國文化最高的理想境界。
與對普遍和諧的追求密切相關,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平衡性,即它將萬物走向和諧看作是一個趨向于生機平衡即事物的構成要素之間和諧共處、共生並形成相對穩定、協調之均勢的過程。這至少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就世間萬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們均是由既相區別又相滲透從而形成相對穩定均勢的兩方面即陰陽構成的。“陰陽對待”被看作是天地宇宙、萬事萬物基本的存在形態,凡存在的事物都內在地具有既相區別而又相滲透的陰陽兩極。正是陰陽兩極的共處、共生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均勢,構成了天地宇宙、萬事萬物在變動不居中得以保持自身相對穩定性的基本前提。《周易》哲學不僅把陰、陽作爲狀述天地宇宙與萬事萬物的存在與變化形態的基本符號與運行圖式,而且自覺地把陰陽的交互作用上升到了宇宙之基本運行律則的高度來認識,因而有“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論斷。正如《莊子·天下篇》所指出的,“易以道陰陽”。正是依據陰陽學說、以陰陽爲基本範疇並將萬物的形成與變化歸結爲陰陽消息,《周易》得以建構起一個把天地宇宙、萬事萬物均納入由陰陽兩個基本符號組成的六十四卦系統,形成了一個廣大悉備而又變化不已的世界圖式。《周易》之後,運用陰陽模式解釋事物的存在成爲中國哲學共同的範式。在道家看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老子·四十章》。)宋明理學家也認爲,“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是以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張載:《正蒙·太和》)“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朱子語類·讀易綱領》)明清之際王夫之作出了同樣的論斷:“陰陽二氣充滿大虛,此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範圍也。”(《張子正蒙注·太和》)可見,在中國哲學家看來,天地宇宙、萬事萬物無一不是陰陽二氣的産物。陰陽二氣又是互相滲透的。在《周易》中,卦象的變化是因各爻所代表的陰陽的消長所引起的,而正如事物的變化體現爲一個永不停息的過程,陰陽的消長亦是一個永不停息而不斷變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中陰陽的互相轉化並不是忽然之間發生的突變,而是一個在不斷漸變中逐漸積累的此消彼長、互相滲透的過程。《周易》卦象的變化典型地表徵了陰陽互相滲透的原理。對此,其後的中國哲學家更是作出了明確的理論概括。《黃帝內經》明確提出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金匱真言》)的命題。這一命題在宋明理學中成爲共識。邵雍指出:“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得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皇極經世·觀物外篇》。朱熹不僅提出了“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朱子語類》卷九十四)的命題,而且明確指出:“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個陰生。”(《朱子語類》卷六十五)陰陽互滲互透,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需、調協而生化萬物,成爲中國哲學世界圖式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本身即是相互滲透的陰陽之間的協調、平衡被看作是天地萬物得以存在的一個基本前提。
其二,就事物發展變化的過程來看,亦體現爲陰陽之間在相互對待的平衡中通過此消彼長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過程。換言之,亦即將事物的變化發展看作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周易》基本的理論意旨,就是要通過將天地萬物的基本存在要素歸結爲陰陽,以六爻、八卦來形象地表徵、類比宇宙萬物及其變化、發展過程,進而揭示範圍天地,廣大悉備,統貫天、地、人三材的根本之道。《周易》的卦爻變化典型地表徵了事物通過此消彼長的不平衡變化而走向新的平衡與和諧的過程。中國哲學的這一理論特質在“陰陽五行”論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在中國文化中均有著久遠的觀念根芽的陰陽說與五行說在經過長期的各自發展後,在春秋戰國時代經過以鄒衍等爲代表的陰陽家的綜合而融爲一體,形成日後被看作是中國哲學中的宇宙運行模式的“陰陽五行”論。五行之氣被看作是從屬於陰陽之氣並由陰陽二氣産生。這個圖式的基本特點,是以陰陽爲事物運動變化中的內在生命力量而以水、火、木、金、土“五行”作爲事物運動變化的外在質料,並以此爲基本的觀念框架來把握天地宇宙的靜態構成與動態變化。在“陰陽五行”論中,世間萬物的發展變化均被歸結爲由陰陽二氣的不斷消長與水、火、木、金、土“五行”之間的不斷生克所形成的永不停息地在動態中求得平衡的過程。對此,董仲舒作了有代表性的論述:“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五行者,……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比相生”指五行中相鄰者相生,即董仲舒所謂“木生火,水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所謂“間相勝”,指五行中相間隔者相勝,即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漢代之後,陰陽五行說成爲中國哲學理解天地宇宙的基本觀念框架。這個觀念框架有兩方面的基本要點:其一,宇宙萬物均是由陰陽消長和五行生克而産生的,離開了陰陽消長和五行生克,天地萬物就不可能存在。其二,五行生克是同一變化過程中兩種既相互聯繫而又相互制約的力量,兩者缺一就不可能有生存變化。自然之道、人事之理、生命之則,都是陰陽互補互動、五行相生相剋。陰陽如果不能達到動態的平衡,就失去了“陰陽大化”的秩序性,從而陷入失序狀態,就會出現天災人禍、疾病等。這說明,在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中,事物的存在與變化就是一個不斷達到動態平衡的過程。
其三,就對事物發展趨勢的價值取向來看,中國哲學特別注重“中”即構成事物的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狀態。這一理論趨向同樣在《周易》哲學中已有端倪。正如有論者已指出的,“《周易》特別強調時中的觀念,全書有三十五處言中,有二十四卦言時,這正是以一陰一陽的觀點看生命所要求的,因爲時中的概念表達了陰陽平衡的狀態。《周易》哲學告訴人們,生命即時中,違背時中,生命也就不存在了。”⑷所謂“時中”,亦即隨時而中,即隨應時空條件的變化而動態地達到“中”。《易傳》高度稱賞“中”,不僅把天地宇宙看作是一個生生不息、變化不已的生命體,而且以“中”作爲其運動、變化的根本律則。《彖傳·臨》:“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彖傳·無妄》:“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正是《周易》開啓了中國哲學“尚中”的價值取向,在日後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學說和理念。而正如朱熹所指出的,“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個恰好的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朱子大全》文三十一《答張敬夫》。)可見,所謂“中”實際上就是構成事物的諸不同要素之間所達成的精妙平衡。如果說中國哲學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話,那麽,“中庸”則至少包含了爲人處世以“適度”(無過無不及)爲原則、通過各種不同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上的和諧統一(和而不同)、隨時而中(時中)等三方面的基本內容⑸。這其中所追求的,不僅是有機的平衡,而且是動態的平衡。
與和諧性、平衡性相聯繫,穩態性構成了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的第三個重要理論特質。這裏所謂“穩態性”是指,中國哲學並不象現代性思維那樣,明確認爲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運動變化過程的推進,事物必然會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體現爲不斷從較低層次發展到更高層次的“進化”,而是更傾向於把事物的變化主要看作是一個從不平衡狀態走向新的平衡狀態的“類迴圈”過程。筆者認爲,把中國哲學傳統中的事物變化模式在精神實質上同樣歸結爲是不停歇的“進化”,恐怕是按現代性思維的主導觀念對中國哲學傳統的“過度詮釋”。在我們看來,儘管中國哲學對事物變化規律的理解確實亦包含了發展和進步的內容(如《周易·系辭》指出:“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所謂“日新”、“生生”顯然都包含了創新和發展的內涵。),但這方面不僅不是中國哲學關注的重心,而且也不足以充分說明中國哲學是把世界的變化看作不斷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進化的過程。這有以下幾點理由。其一,儘管中國哲學傾向於將世界看作是由體現了生機與活力的萬事萬物所構成的生命的“一大流行”,並明確肯定了天地宇宙、萬事萬物運動變化的永恒性,但這是否意味著天地宇宙是處在永恒的“進化”過程中?這在中國哲學中似乎是一個“六合之外”因而“存而不論”的問題。與中國哲學的思想主題與思維方式相聯繫,歷代思想家大多著力于立足人世而從微觀層面來觀察與言說具體事物的“變”與“化”,很少有人從總體上對天地宇宙是否永恒“進化”的問題作出正面回答。其二,正如上文已論及的,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十分注重和諧和平衡,事物的運動變化被看作是一個既有的和諧和平衡被陰陽的消長與五行的生克所帶來的不和諧和不平衡所打破,並在陰陽的繼續消長與五行的繼續生克中走向新的和諧與平衡的過程。它更爲強調事物運動變化中穩定性的一面,並且至少在形式上採取了循環論的方式。其三,如果說中國哲學史上鮮有人作出過“天地宇宙是處在永恒的進化過程中的”的論斷,注重“平衡之穩態”的言論則不僅多有所見,且更有人明確提出了迴圈範式。中國哲學中的基本形上預設即“萬物同出於道而又歸根結底複歸於道”就是“平衡之穩態”而非直線式發展的。《周易》哲學“反復其道”(《彖傳·複》)、“原始反終”(《易傳·系辭》)的觀念體現了這一點,《老子》“反者道之動”(第四十章)、“夫物蕓蕓,各複其根”(第十六章)的論斷也說明,“道”不僅是事物的根源,而且亦是事物運動變化的終極。同樣,中國文化的主流形態以“天人合一”作爲自己的理想境界更是自覺保持“平衡之穩態”的表現。與此同時,不僅在歷史觀而且在宇宙論圖式方面均有明確提出“循環論”者。早在春秋戰國時代鄒衍就提出了“五德終始”的歷史演變論。他“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認爲王朝更替乃至社會興衰均是隨著土、木、金、火、水五德依次相克而轉移迴圈的,並徵引從黃帝(土德)到夏(木德)、商(金德)以至周(火德)的變遷以爲佐證。這一歷史觀念把歷史的演變歸結爲按土、木、金、火、水五德依次相克而循環往復,是頗爲典型的循環論。同樣是早在戰國時代,亦已有人提出了循環論的宇宙觀。其中最典型者即《呂氏春秋》的“圜道”圖式。在《呂氏春秋》看來,天地宇宙、萬事萬物的運動變化,都是循環往復的。事物的生長是這樣,“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呂氏春秋·圜道》)晝夜的變化是這樣:“日夜一周,圜道也”(同上)。水的流動也是這樣:“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圜道也”(同上)。概而言之,宇宙間一切事物的運動變化莫不是循環往復的:“天地車輪,終則複始,極則複反,莫不鹹當。”(《呂氏春秋·大樂》)⑹天地萬物的運動變化被看作如車輪之流轉,周而復始、物極必反被認爲是適切於一切運動變化過程而沒有例外的。這不僅是頗爲典型的循環論的宇宙圖式,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哲學對事物運動變化問題的基本認識。因此,與體現了現代性思維之本質特徵的直線式“進步觀”相比,更能體現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之特質的是“迴圈式”的運動變化觀,與其說它是要自覺追求不斷進化,不如說它追求的是要在一定水平上保持平衡的穩態。
三
可見,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在基本世界圖式、基本理論特質方面與現代西方以強調人和自然的二元對立爲基本特徵的世界圖式、以通過對自然的征服和佔有而求得人類社會不斷“進步”和“增長”爲基本理論特質的文化生態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在人類文化面臨根本性變革的“現代之後”,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可以爲未來人類文化的存在形態提供怎樣的有益啓迪呢?我們認爲,這至少包括以下兩方面。
第一,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注重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的基本運行機理,可以爲改變現代性范式下形成的以絕對化地、直線式地追求“永恒增長”爲基本目標的文化生態模式提供某些借鑒。
“進步的歷史觀”是現代性的基本內容之一。在相當程度上,它的出現不僅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而且對促進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的確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但由於這種歷史觀歸根結底是浸潤著“人類中心主義”的,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它不僅逐漸演變成爲“直線式的進步歷史觀”,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被絕對化。人類的現代歷史被描述成直線式的、一往無前地向前推進的過程,人類社會的基本目標就是不斷追求數量的增長再增長,質量的提高再提高。這固然是現代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動力源泉,但它同時也是人類在今天面臨到環境極大破壞、資源逐漸枯竭之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人類中心主義”的主導下,人類對“進步”的絕對化的、直線式的追求,必然會在物質力量不斷增強的同時,也使得人類社會與其依存的生態環境間産生高度緊張。而且正象歷史的發展所體現的,人類社會的發展程度越高,它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就越趨緊張。早在20世紀後半葉,就已出現了關於“增長的極限”與“沒有極限的增長”的爭論。儘管這一爭論至今還未結束,但應當有理由認爲,世界範圍內環境污染與生態危機的加劇已對人類絕對化的、直線式的“增長”方式發出了嚴重警示:如果人類只知道一往無前地追求沒有極限的增長、只能是以對自然的破壞作爲實現自身“進步”與“發展”的前提條件,人類最終將難以逃脫在與自然的尖銳對立中走向覆滅的命運。
因此,面向未來的人類文化必須改變以對自然的掠奪性利用爲自身發展之前提的,以絕對化地、直線式地追求永恒增長爲基本目標的文化生態模式。人類文化的發展目標究竟是不是應當確立在永恒地追求不斷的增長上?這恐怕是一個應當重新加以考量的問題。在一定時空範圍內,我們相信,自然宇宙的發展的確是“永恒”的。因而就理論可能性而言,人類也可以在與自然和諧一體的前提下,隨著自然宇宙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但是,自然宇宙的發展畢竟是一個自在的、緩慢的過程。而具有高度主觀能動性的、以越來越發達的高科技爲依託的人類社會的發展卻不僅是自爲的,而且其加速度是不斷增長的。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作爲自然之異化物的人類始終保持其建立在索取自然基礎上的永恒增長,就不能排除人類的發展將超出自然宇宙發展之承載度的理論可能性。
在對現代性的批判中,後現代主義者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者就提出了“穩態經濟”的觀念⑺。經濟問題固然是“增長”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但它只是一個表現形態。要“治療增長癖”,僅提出“穩態經濟”的觀念是遠遠不夠的。歸根結底,這涉及到文化生態模式從價值理念到制度性的中間架構再到技術與物器層的方方面面。因此,要改變的是文化生態模式本身。而在這方面,中國哲學傳統應當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鑒。
前文已述及,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構成了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的基本運行機理。概括而言,無論是和諧性、平衡性還是穩態性,其根本的意旨都是要保持構成文化整體系統的各內外要素(這其中理當包括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良性迴圈關係。毋庸置疑,正象中國傳統社會所顯示出來的,中國哲學的這種文化生態模式自有其內在的局限,在現代觀念的比照下,對此可以認識得更爲清楚。這種文化生態模式儘管的確內在地蘊涵了“可久”、“可大”之道,但由於它是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早期就已出現的,是建立在較低的物質生産力水平之上的,因而其“平衡之穩態”就只能是把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維持在較低層次上,只能是在整體上遲滯中國社會的發展程度。但是,當從“現代之後”的視野來對這一文化生態模式予以重新審視時,它的基本理論特質與運行機理是否可能爲已在總體上得到高度發展的人類社會尋求一種新的文化生態模式提供某種有益的啓示呢?站在謹慎樂觀主義的立場上,人類社會在經過長期發展後在一個相當的高度上保持一種平衡的穩態而不是強調永恒的增長,或許將不失爲一種更爲清明而理性的選擇。
第二,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內含的價值系統,可以爲面向未來重建人類與自然的健康關係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個哲學系統的文化生態模式與其內含的價值系統無疑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中國哲學的文化生態模式之所以以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爲其基本的運行機理,不僅與中國哲學所突顯的“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的世界圖式、力圖在構成文化整體系統的內外要素之間保持良性迴圈關係的基本價值取向有著內在的一致性,而且也是依託於中國哲學通過“內在超越”之路而達於與天地精神相契合之境的終極關懷價值系統的。要根本改變人類文化的存在形態,不僅要改變文化生態的運行模式,而且亦必須變革人類文化生態模式所立足的基本價值系統。在某種意義上,如果說前一方面是停留在“技”的層面,後一方面則已“進於道”。因而,後一方面應當說具有更爲根本的意義。儘管後現代主義等西方當代思潮已對改善人類與自然之關係的必要性有了較爲清楚的認識,並提出了“自然的返魅”⑻、實現從“人類中心主義”向“生態中心主義”的轉變⑼等種種解決之道,但由於這些理論大多是直接針對生態危機主要從工具理性的視角來予以論說,因而不僅很難在理論上真正透闢地解決問題,而且還招致了一些批評意見。如在對自然界是否具有“內在價值”的討論中,有的論者已指出,自然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觀有著自身難以逾越的理論困境,其中的理論關節點在於:自然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觀的理論基礎是要從“是”中直接推導出“應當”,而這卻是已爲西方古典哲學理論和20世紀元倫理學證明不可能的。因此,自然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觀是不可能成立的,人類之所以要保護生態自然,“最終是出於對人類全局的、長遠的生存利益的終極關懷。”⑽應當說,從“是”中不能直接推出“應當”的論斷是符合西方哲學傳統的。但由此認定人類只能從自身利益出發來“保護生態自然”,則依然是在人與自然二分對立的現代性思維框架下主要從工具理性層面來思考問題。而要真正爲面臨深刻的生態危機的當代人類文化尋求到面向未來的康莊大道,衝破人與自然二分對立的現代性思維框架、在終極關懷的層面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恐怕應當成爲基本的理論前提。
在這方面,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或可提供有益的借鑒之道。不同於西方當代思想流派對生態問題的思考主要是立足於工具理性的層面,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的基本世界圖式,以強調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爲基本特色的運行機理,力圖在構成文化整體系統的內外要素之間保持良性迴圈關係的基本價值取向則是直接生髮於其終極關懷價值系統的。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的有關思考歸根結底是立足於價值理性因而是超工具理性的。這一基本的立足點與思維框架可以爲進一步思考當代人類所面臨的文化生態問題提供更爲開闊亦更爲厚重的理論視野。與此相關聯,“內在的人文主義”可以爲面向未來重建人類與自然的健康關係提供一條不同於西方式的解決之道。即以“自然是否具有內在價值”以及“是”與“應當”的關係而言,立足於中國哲學的智慧精神完全可能作出另外的回答。在西方哲學中,人是外在于自然的,因而“自然的內在價值”問題的確是難以通過理性的認知來加以肯定的問題。但在中國哲學中,人是內在于自然的,人的價值與自然的價值在一定程度上無疑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因而“自然的內在價值”恰恰可以看作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問題。同樣,由於人與天地宇宙的互爲內在性,中國哲學中的“是”與“應當”或曰“存在”與“價值”亦有著本然的一致性。即以《周易》對“生”的言說而論,當它稱言“生生之謂易”時,可以說是對“存在”的言說;而當它作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論斷時,則顯然已是對“價值”的言說了。而在《周易》中,這兩者恰恰是聯屬爲一體的。中國哲學雖然沒有也不可能在知識論的層面從“是”直接推出“應當”,但它卻的確在存在論的層面“開顯”了“存在”與“價值”的內在統一性與原始統一性。中國哲學“內在人文主義”對今天人類進一步思考文化生態問題所可能提供的啓迪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四
本文主要集中討論了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所可能有的“後現代”意義。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由於論域以及篇幅所限,本文沒有對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所具有的局限作出具體的理論分析。但這並不表示論者認爲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是沒有缺點的。同樣,我們集中討論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所可能有的“後現代”意義,並不意味著認爲西方現代的文化生態模式是沒有意義的,更不是主張“只有中國文化能夠拯救世界”。本文所論的一個基本立足點是:在人類文化應當亦必須走出“西方中心論”並通過新的綜合與新的創造以集中全人類各文化共同體的智慧來解決“地球村”面臨著的共同問題乃至危機的“現代之後”,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可以爲未來人類文化的存在形態提供怎樣的有益啓迪?
注釋:
⑴成中英教授對此先後有不同的歸納。《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與世界化》(北京和平出版社,1988)一書用的是“內在的人文主義”與“外在的人文主義”,而《合外內之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一書則是“包容性人文主義”和“排它性人文主義”。筆者認爲,兩組術語中似以“外在的人文主義”和“內在的人文主義”更爲妥帖。理由有二。其一,“排它性”和“包容性”雖有一定對應性,但由於詞義上的模糊性,兩者的區分在邏輯上並不完全周延。“外在的”與“內在的”的對應則顯然更嚴整。其二,“內在的人文主義”不僅比“包容性人文主義”更能準確地狀述中國哲學人文主義的基本理論特質,而且對今天學界關注的自然界的“內在價值”問題具有更直接的理論針對性。
⑵參見成中英:《世紀之交的抉擇》,第173–201頁,上海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
⑶詳論參見蔡仁厚:《孔孟荀哲學》之“孔子之部”,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版。
⑷施忠連、李延佑:《論〈周易〉的生命哲學》,《周易研究》1998年第4期。
⑸詳論參見李翔海:《生生和諧—-重讀孔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3頁。
⑹參見方立天:《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第156–157頁,中華書局1990年版。
⑺參見格裏芬編、王成兵譯:《後現代精神》,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85頁。
⑻參見大衛·格裏芬編、馬季方譯:《後現代科學》,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
⑼參見Albert Schweitzer、Aldo Leopold、Arne Naess等關於“生態中心主義”的論著。其中有的已有中譯本,如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Aldo Leopold的《沙鄉年鑒》,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⑽劉福森:《自然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觀的理論困境》,《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
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概念和馬克思的實踐概念
徐長福
內容提要:爲了探尋馬克思主義實踐思想和西方實踐哲學傳統的內在關聯,本文較爲詳細地考察了亞裏士多德的實踐概念和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及其聯繫。亞裏士多德是西方實踐哲學的創立者,他把人類知識和活動三分爲理論、實踐和創制。其中,理論主要指求知自然的普遍原理的思想活動,實踐主要指追求倫理德性和政治公正的行動,創制主要指生産生活資料的勞動。理論和實踐都以自身爲目的,是自由人從事的活動,創制則以其産品爲目的而以自身爲手段,主要是奴隸從事的活動。馬克思把亞裏士多德的勞動和實踐結合起來,一方面把勞動的生産性看作包括實踐在內的人的全部生命活動的本性,從而把人類歷史看作人類自我産生的過程,另一方面把實踐的目的性看作勞動的本質,把勞動從充當手段到充當目的的變化看作歷史運動的價值指向,從而爲勞動和勞動者的解放,爲人類的普遍自由提供了本體論基礎。此外,馬克思還從實踐出發將科學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所以,馬克思的實踐思想在西方哲學史上不是一種斷裂式的革命,而是對亞裏士多德所開創的西方實踐哲學傳統的綜合創新。
引言
近些年來,在我國的哲學論壇上,悄然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實踐哲學話語:一種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的實踐哲學話語,一種是西方哲學學科的實踐哲學話語。前一種話語大家都很熟悉,其中,實踐主要被理解爲人改造世界的物質性活動,二十多年來存在的爭議只是:本於史達林模式的教科書哲學將實踐放到認識論中去理解,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實踐唯物主義”則將實踐看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一個“准本體論”性質的核心概念。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對實踐問題的理解至今基本上沒有超出這一話語模式。由西方哲學學科所引入的後一種話語多數人可能還比較生疏,其中,實踐主要被理解爲一種倫理性活動。從學派上講,解釋學進路的實踐哲學可能是這一話語中的最強音。加達默爾明確提出的“作爲實踐哲學的解釋學”[lvi]已被我國一些學者詳細地介紹了進來,這些學者對有關主張還大多給予了積極的回應。[lvi]另外,麥金太爾在其被譽爲“倫理學研究的新的轉捩點”的《德性之後》一書中也提出了一種實踐觀念,[lvi]並作爲其倫理學理論建構的基礎。他的觀點在我國學界也有相當的影響。這些學派的一個共同的顯著特點就是回到亞裏士多德的實踐哲學中尋找理論資源。於是,在我國學界,儘管這兩種實踐哲學話語都講實踐,都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但其各自所言說和意指的東西實際上差異極大,有時甚至顯得難以溝通。
上述局面客觀上向我們顯示了一個重要的課題,這就是弄清這兩種實踐哲學話語的關係,並進而弄清這兩種實踐哲學話語跟西方實踐哲學傳統的關係,以及弄清各種實踐哲學理論跟當今中國以至整個人類所面臨的基本實踐問題的關係。這也就是要求我們在一個更加深廣的學術基礎和理論背景上對實踐問題和實踐哲學作一個貫通的理解。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概念和實踐思想原本就是從西方實踐哲學的傳統中發展出來的。對於這一點,過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結果就形成一種印象:似乎西方哲學只是到了馬克思才有了真正的實踐哲學,馬克思主義跟先前哲學的根本區別就在於馬克思主義是改變世界的實踐哲學,而先前的哲學只是解釋世界的理論哲學。另一方面,當代西方哲學所講的實踐,跟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思想也並非毫無關聯,不僅二者都源於同樣的實踐哲學傳統,而且它們還共處於當代人類複雜的思想文化觀念的結構系統裏。就此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的學者不能繼續安于不理會西方實踐哲學的傳統而談論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同樣,西方哲學學科的學者也不能無視或回避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思想而安於一套別樣的實踐哲學。特別是對於我們這個圍繞實踐一詞積澱了太多酸甜苦辣體會的民族來說,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思想和當代西方的實踐哲學以及整個西方實踐哲學傳統從學理上加以認真的清理,一定大有裨益。
本文就是基於上述認識而開展的一項系列研究的一部分。對於實踐哲學研究來說,弄清實踐概念是第一步工作。由於亞裏士多德被公認爲西方實踐哲學[lvi]的創始人,馬克思則是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創始人,並且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是從觀念到實際都距離我們最近的實踐哲學,因而筆者擬從頭開始,在本文中對二人的實踐概念及其關係作一系統考察,爭取將其間的聯繫與區別呈現出來,以作爲進一步探討的基礎。
一、亞裏士多德的實踐概念
1.實踐概念出現的問題背景
實踐,不論人們賦予它的含義如何紛紜複雜,就其最具公共性的含義來講,其所指應是人的活動,並且是人的有別於觀念活動的實際行動。這一點應該是可以確定的。這樣一種活動進入人類的思考視野,被人們作爲理智探討的物件,或者說被哲學主題化、課題化,是一個漫長歷史過程的産物,是人類生活綻開到一定程度的思維結果。即使把實踐問題放到哲學史中考察,我們也能發現,哲學家們一開始並沒有注意到實踐問題,只是到了後來,當實際生活的震蕩將舊有的問題震出些裂縫之後,人們才逐漸有所分辨,並將其中某些問題命名爲實踐問題。指出這一點,是爲了說明:爲什麽實踐哲學沒有開端於哲學誕生的時候,而是開端於亞裏士多德?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我們理解亞裏士多德的實踐概念的前提。
按照哲學史家通常的看法,希臘哲學在蘇格拉底以前主要是自然哲學,到蘇格拉底發生了人的哲學的轉向。如果作粗淺理解的話,似乎這種轉向主要是研究物件的變換,即先前的哲學家主要研究自然,而蘇格拉底則開創了一種主要以人自身爲研究物件的哲學潮流。其實,所謂自然哲學,決不僅指一種研究物件,更重要的是指一種理解世界的哲學觀念。在這種觀念看來,世界,包括人,歸根到底是一種自然而然成長和變化的東西,是一種本性上就有力量成爲“如此如此”的東西。這也是自然(physis)一詞的本義。[lvi]這裏,人爲的東西儘管作爲生活現象存在著,但尚未在哲學層面上凸顯出來跟今天被稱爲自然界的東西相對置。所以,儘管自然哲學家也探討社會與人生,但在他們那裏,並不存在那種在本性上跟自然問題不同的人的問題,當然也就不存在實踐問題了。
西元前五世紀的希波戰爭對希臘人震動很大,它向希臘人深度展示了非希臘世界的制度、法律和風俗,讓他們意識到了原來人們的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東西是可以因時、因地而異的。這樣就有了所謂physis(自然)和nomos(習俗)的區分,並進而促成了智者運動中的相對主義觀念的出現。[lvi]人的東西和自然的東西都是可變的,但自然的東西的變化是自然而然的,而人的東西的變化可以加入人的選擇的因素。於是就發生了“世界應該怎樣”的問題,這個問題跟“世界是什麽”的問題是不一樣的,儘管這一點當時的人們尚未明確意識到。蘇格拉底所要解決的就是如何給一個被相對主義搖動起來的習俗世界(即由人的生活中那些可以人爲的因素所構成的領域)重新奠立一個價值基礎的問題。在這裏,一個明顯有別于先前自然哲學觀念的新的意識産生了,人的問題的本性呈現出來了,從而實踐問題也就暗含在其中了。
有別于自然問題的人的問題的主題化,其實質在於追問:人在可以自爲的行爲中據以抉擇的根本原則究竟是什麽?這種追問顯然不同于自然哲學對本原的追問。或者說,蘇格拉底所追問的實質上是“應該”的問題。不過,蘇格拉底意在超越那些雜多易變的生活現象而達到某種普遍恒定的原則,這跟自然哲學家尋找不變本原的思維方式又具有相同的品質。這種既別于自然哲學又一定程度地同于自然哲學的工作被柏拉圖推到極致,其結果就是建構了一套表達人爲世界之應然性原則的理念(idea,eidos,或譯爲“相”)系統,這套系統同時也是對人的世界“是什麽”的回答。柏拉圖晚年甚至將自然問題也一併考慮進了他的理念系統中。這樣一來,physis和nomos,或者說自然做主的領域和人做主的領域,就從“應該”的原則出發得到了新的統一,儘管這種統一顯現爲一個“是”的系統。
柏拉圖的做法遇到了新的障礙。這不僅在於“是什麽”和“應該怎樣”這兩類問題是否可以統一(比如那些在價值上被否定的東西是否也有理念),而且在於人類可以自主的領域是否可以有效地爲一套理論原則所統制。這些障礙迫使柏拉圖的後期思想一方面朝著鞏固理論統一性的方向發展(如前述將自然領域也納入理念論的體系),另一方面朝著尊重特殊性的方面調整(如《法律篇》就頗有將《理想國》的理論原理與政治生活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意味)。其結果是,從自然哲學的遮蔽中綻露出來的不同于自然問題的人的問題,又從柏拉圖的理念論的重新遮蔽中再次綻露出來。實踐便是從這種特殊的人的問題的再次綻露中所萌生出來的概念。
儘管在亞裏士多德之前已經有人探討過實踐問題,比如希波克拉底就曾論述過醫療實踐和醫學理論的關係,[lvi]柏拉圖也對置地使用過“在實踐中”、“在活的生活中”和“在理論中”,[lvi]並區分過技術製造的知識和教育文化的知識,[lvi]柏拉圖跟畢泰戈拉學派的歐多克索和阿爾基塔還就理論知識及其應用問題發生過爭論,[lvi]但他們或者完全沒有在上述問題背景中討論問題,或者對該問題背景尚未達到充分的意識。關於亞裏士多德的實踐概念和柏拉圖有關思想的關係,後文還要涉及。在柏拉圖的基礎上,亞裏士多德明確提出了實踐概念,並建構了歷史上第一套實踐哲學的理論體系,其根本用意就在於要給這個由人自主的領域從學理上加以說明。馬克思的實踐思想和當代西方實踐哲學都是類似問題情境的産物,因而跟亞裏士多德的實踐哲學之間具有內在的關聯。
2.人類活動的三分法
亞裏士多德曾在多種含義上使用過實踐一詞,但其最確定的用法是將人類活動一分爲三。在《形而上學》第六卷中,亞裏士多德將思想分爲實踐的、創制的與理論的三種,並對人的知識和學科門類也作了相應的區分。[lvi]進而,人的活動、生活領域和目的等的區分也蘊涵其中了。亞裏士多德在其他許多地方對有關區分從不同角度給予了充分的闡述。有西方學者將這種三分法整理成如下樣子:[lvi]
| 理論領域 | 實踐領域 | 創制領域 | |
| 1.活動 | 觀察(view) | 行動(act) | 做(doing) |
| 2.知識類型 | 科學(science) | 深思熟慮(deliberation) | 技藝(skill) |
| 3.達到的目的 | 幸福(happiness) | 恰當的生活(proper life) | 福利(welfare) |
亞裏士多德的這種三分法決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活動類型區分,它的根本用意在於從學理上對前面所指出的背景性問題加以回應。
在希臘哲學史上,巴門尼德將人類知識劃分爲對應於存在(to be,或譯爲“是”)的思想和對應於非存在(not to be,或譯爲“不是”)的意見,並倡導走真理之路而不要屈從於來自衆人的經驗習慣。[lvi]這裏,關於物件的真理性認識是最高的活動,甚至是唯一有意義的活動。如果還有實踐活動可言的話,那也只能屬於沒有真理性意義的意見的範疇。在此基礎上,柏拉圖將世界劃分爲理念的世界和感性個別事物的世界,後者因分有或模仿前者而獲得存在及其意義。據此,把握理念的知識是真理,有關的活動具有最高的價值,而把握具體事物的知識只具有真理的摹本的價值。柏拉圖不同于巴門尼德的地方在於他賦予了理念認識之外的其他人類活動與知識類型以一定的合理性,儘管這種合理性是由理念認識的合理性派生出來的。柏拉圖對人類活動與知識類型有許多不同的劃分方式,但其基本劃分原則是一貫的。
亞裏士多德的三分法跟巴門尼德和柏拉圖的觀點的一個顯著區別就在於:亞裏士多德已經注意到了實踐和創制活動跟理論活動之間在本體依據上具有某種差異性,相比之下,巴門尼德只是強調了思想和意見的區分而尚未考慮其間的關聯問題,柏拉圖則將各種相對劃分開來的活動從本體論上統一到了對理念的認識之中。亞裏士多德觀點的創新之處在於:他沒有把實踐和創制從邏輯上還原爲理論,或從理論的本性去統一地說明實踐和創制的本性,而是把實踐和創制看成跟理論雖有聯繫但又有重大區別的其他類型的活動。
在亞裏士多德的三分法中,理論(theoria)依然具有優先的地位。理論指一種沈思活動,人通過這種沈思而達到對世界的不變的原因和原理的認識。最高的理論爲第一哲學,處理的是最高層次的原因和原理。這種原因和原理最接近神性,對之加以研究的意義就在於這種研究直接就是人超越自己有限的存在而契合神性的方式,所以它是人最高層次的活動。亞裏士多德給理論的定位跟整個古希臘哲學傳統是一致的。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理論活動能夠有效地涵蓋或推出其他活動,亞裏士多德是不會再搞一套實踐哲學的。
理論所把握的原因和原理是自然中的普遍性,如果足夠真實的話可以適用於相關領域的一切物件。但關於人的行爲的認識卻不然,沒有任何一條政治、法律或倫理規定可以普適於人的一切行爲。柏拉圖晚年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lvi]造成理論原則不能有效覆蓋人的行爲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人的選擇性。人在行爲中既可以選擇這樣做也可以選擇那樣做,從而就跟所有的其他存在物的運動區別了開來。出於這種考慮,亞裏士多德將經濟學、倫理學和政治學看成跟數學、物理學和第一哲學不同的另外一類科學,它們以人的行爲作物件,探討在有人的選擇因素參與其中的情況下人的行爲如何趨向好的目標。這三門學科所研究的物件便叫做實踐(praxis)。其中,雖然政治學在目的層次上是最高的,但倫理學卻是最基本的,因此倫理學意義上的實踐是最基本的實踐。
一般地講,實踐和理論的區別在於:理論的本性是求知,實踐的本性是求好(good,即善);理論的特點是沈思,實踐的特點是行動;理論的求知只能通過對普遍性的沈思來獲得,實踐的求好只能通過對特殊性的操作來達到;理論科學的意義在於提供知識,實踐科學雖也提供知識,但根本意義不在於知識,而在於使人們實際地變好。深一層講,理論求知的最終根據也在價值上,因爲最高的存在也是價值上最好的存在,即神,人求知最高的存在目的在於分有它的好。[lvi]在這個意義上,理論跟實踐的區別在於:理論是知自然和神的好,而實踐是行人自己的好。在柏拉圖那裏,知好和行好是統一的,因爲人的行動是對理念的摹仿;而在亞裏士多德那裏,知外部事物的好和人行自己的好、擁有關於好的知識和自己實際地變好是兩回事。如是,理論和實踐之間就具有了真正的異質性,儘管這種異質性在亞裏士多德那裏還是十分有限的。同時,這兩者間的關係也不是後世流行觀念中的基本原理及其應用的關係,而是兩種活動或生活領域的外在並列的關係。實踐僅僅由於其知識達不到理論知識的普遍性程度,才等而次之。不過,實踐和理論又具有共同點,這就是:他們都是以自身爲目的的活動。也就是說,理論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用以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實踐也以自己爲目的,而不以別的東西爲目的。這一點跟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和當代西方實踐哲學的實踐概念都具有本質性的關聯。這兩種活動也是古代希臘人的觀念中真正值得從事的活動,是真正符合人的價值尺度的活動。[lvi]
這樣就引出了與實踐相比照的第三種活動,即創制(poiesis)。在英語學界,有的學者將實踐譯爲act而將創制譯爲doing(如上述表格中那樣);另一些學者則將實踐譯爲doing而將創制譯爲making。[lvi]儘管有這些差異,但對意思的理解大體上是一致的。實踐主要是指倫理與政治行爲,創制主要指生産和技藝活動,特別是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活動。實踐的目的在於其自身的好,創制的目的在於其産品的好。[lvi]比如,道德修養的目的就是把道德修養好,兩者是一個東西;建造房屋的目的則是一座建成的房屋,建造活動跟建成的房屋是兩個不同的東西。也可以說,實踐是無須結果的花,開花本身就是目的;創制則必須結出果實,開花只是手段。但這兩種活動也有重要的相同點,即它們都是人的自覺行動,都有人的選擇性、人的作爲參與其中,都跟具體的個別物件打交道,都關聯著和構造著一片非自然的自主生活領域。相比之下,創制比實踐更接近於馬克思主義學統中所流行的實踐概念,而當代西方實踐哲學的實踐概念主要使用的是亞裏士多德實踐概念的原義。這之間的複雜關係已經依稀可辨。
亞裏士多德區分實踐和創制的根本用意在於將目的性活動和手段性活動、自由的活動和出於自然必然性強制的活動加以剝離,而這種剝離的社會制度基礎與文化觀念基礎就是當時希臘世界的奴隸制及其相應的意識形態。在當時的希臘世界,除農業之外的生産勞動幾乎由奴隸包攬,即使勉強列入體面活動的農業勞動也往往由最下層的自由人來從事。手工業與服務性行業則主要由沒有公民身份的外邦人來從事。這些活動或繁重或瑣屑,其創造的産品往往直接關乎人的肉體生存,而肉體生存對人來說僅僅是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手段。在這個意義上,創制只是實踐的手段,奴隸只是主人的手段,工匠只是雇主的手段。實踐和創制的劃分對應著主人和奴隸、雇主和工匠的劃分。[lvi]從這個角度去看,後來的康得的實踐哲學,在盧梭等人的平等理念的影響下,就是想消除充當目的的群體和充當手段的群體的差別;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則想解決手段性活動和目的性活動的矛盾;當代西方實踐哲學則想矯正目的性活動和手段性活動之間的失衡。由此足見亞裏士多德劃分實踐與創制對整個西方實踐哲學的巨大影響。
要進一步說明何以人的自主活動領域蘊涵著手段性活動和目的性活動的分離,還須回到前述physis和nomos的關係問題。physis的領域,或純粹自然的領域,是人的作爲無能爲力的領域,人跟它之間只有發生純粹認識的關係時才能獲得自由和幸福的感受。在nomos的領域,即人的自主生活領域,人的自由和幸福感受則直接寓於人的選擇行爲當中。然而,人又是一種兩重性的存在物,他既有自然的一面,又有自爲的一面,並且自爲的一面一定要以自然的一面爲基礎。這樣一來,人就必須再有一種活動,它不是靜觀自然,而是通過人的身內自然實際地作用于身外自然從而克服自然必然性對自己的束縛,並爲自主生活領域創造條件。這樣一來,由自然的必然性所首先導出的活動就是人謀求生存資料的活動。這種活動固然是人的自覺的活動,卻是由自然必然性所強制的活動。或者說,它創造著自由,但本身尚處在努力掙脫必然性的階段,所以它只是自由的手段。在這種活動所建構的生命平臺上,人可以從事不由自然必然性決定而由自己的意志決定的活動。不過,意志活動有一個不足,這就是不確定性,而這一點則可在人理性地沈思自然及寓於其中的永恒不變的必然性道理中得到彌補。人最終在自由的思考中跟自然的永恒性的一面統一起來,從而實現向著神性的超越。可見,自然做主的世界同時關聯著人的理論活動和創制活動,由人做主的世界同時關聯著人的實踐活動和創制活動;目的性領域同時關聯著人的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手段性活動只與創制活動有關。這些就是亞裏士多德三分人的活動的內在理據。有關分析可以整理成下表:
| 目的性活動 | 手段性活動 | 把握普遍性的活動 | 把握特殊性的活動 | |
| 與自然有關的活動 | 理論 | 創制 | 理論 | 創制 |
| 與人的自主生活有關的活動 | 實踐 | 創制 | 實踐創制 |
正因爲亞裏士多德的三分法是出於上述考慮,所以他才把以自然所成的事物作爲沈思物件的學科稱爲“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lvi]亦即“自然哲學”或“物理學”(physica, physics),而把以實踐爲物件的科學稱爲“人的哲學”(human philosophy)。[lvi]另外,他還把第一哲學叫做神學(theology)。[lvi]加上創制之學,便大體組成了亞裏士多德的學科骨架。
3.特點與問題
亞裏士多德的實踐概念最明顯的一個特點是:它凸顯了人類生活中的一個以自身爲目的的行動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行動是由人自主選擇的,且本身就是目的。這個領域是亞裏士多德透過柏拉圖哲學的破綻而發現的,是他的一個理論貢獻。在此之前,只有理論活動才被看作目的性活動。儘管亞裏士多德也繼承了傳統看法,並把理論活動看作最高層次的目的性活動,但理論活動是沈思而不是行動,是想而不是做,是在觀念上契合最好的外部存在而不是在實際中實現人自己的好,所以,亞裏士多德將行動、做看作跟理論活動並列的目的性活動,是一大創新。這一思想對後世的西方實踐哲學,包括馬克思的實踐哲學,都有明顯的重大影響。
實踐之所以被另列爲一種目的性活動,從消極方面講,是因爲它不能被整合到理論活動中去。理論作爲活動是自由的,只有那些免於勞作之苦、事務之煩的有閑階層才可能從事這樣的活動,或者說只有那些免於行動的人才能從事理論。[lvi]但理論的物件卻是普遍必然的東西,亦即非自由的東西。實踐與之不同。實踐作爲行動已經包含了選擇上的自由,儘管這種自由因不能從行動中抽象出來而不如理論活動中的自由那樣純粹,[lvi]但它畢竟不是那種由必然性所支配的運動。更重要的是,實踐活動和實踐的物件是同樣的東西,即都是有自由的東西。如是,實踐的性質跟理論的性質之間就既不是同一的關係,也不是包含的關係,而是交叉的關係,這就使實踐得以獨立於理論而自成一種目的性活動。在這裏,我們不難看到康得問題的萌動。
實踐成爲目的性活動,從積極的方面講,跟創制活動被打入另冊直接相關。創制本來意味著人的自覺的作爲,應屬自由的活動,但由於創制概念所指的活動主要是生産性勞作,而這種活動均由自然所施加給人的必然性強制所引起,因而它只是創造自由但自身尚不自由的活動,或者說只是指向自由的活動。對創制而言,自由、目的均不在活動本身,而在活動的結果。正是這種結果從創制者向非創制者的轉移和非創制者對這種結果的佔有和享用,才爲其自身即是目的的實踐活動和理論活動搭建了自由的平臺。這裏便埋下了馬克思實踐思想的伏筆。
亞裏士多德的實踐概念的問題主要在於實踐跟創制、創制跟理論、實踐跟理論的多重分離。後世實踐哲學所要解決的主要就是這些分離問題,儘管有些解決又造成了新的分離。
本來,實踐和創制都屬於行動的領域,跟理論之爲沈思的領域正好可以對置地看待。但亞裏士多德出於價值理想方面的考慮而將二者區別開來,這樣就在觀念上塑造了純粹目的性的行動和純粹手段性的行動的對立關係,進而爲實際生活中從事純粹目的性行動的社會群體和從事純粹手段性行動的社會群體之間的對立提供了理論支援。這樣一種劃分跟柏拉圖在《國家篇》中將兩個統治階層的政治活動跟第三階層的生産活動區別開來,以及跟孟子將勞心者治人的活動和勞力者食人的活動區別開來,具有價值意圖上的一致性。亞裏士多德還不可能看到的是:不是高貴的實踐而是低賤的創制在近代以後改變了歷史。其間的奧妙後來被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講主奴關係時首次揭示了出來。創制活動的威力的勃發改變了人與自然、人與人的舊有關係,從而爲近代以後的思想家們,特別是馬克思重新考慮創制與實踐的關係提供了可能。
在亞裏士多德的三分法中,創制和理論在價值上距離最遠:理論是最高貴的活動,創制是最低賤的活動。在希臘人的觀念中,進入政治活動才算進入了真正人的領域,“前於政治”的活動也就是“前於人”的活動,創制正是這種“前於人”的活動。[lvi]相比之下,理論就是“超於人”的活動,也就是“近於神”的活動。在這種觀念背景下,不存在理論服務於創制的問題。儘管亞裏士多德明確討論過理論和創制的內在聯繫問題,比如,他認爲,技術高於經驗的地方就在於它包含了普遍的知識,但是,他的意圖不在於說明理論對技術有用,而在於描述從經驗到技術再到理論的價值序列。[lvi]理論跟創制的分離,既是一種觀念,也是當時的生活實際。但不管怎樣,這種分離使得人類把握普遍性的理性能力無法轉化爲改造世界的實際力量。這個問題一直等到弗·培根的時候才得到解決,他的“知識就是力量”的思想將一種可以結出果實的活動和一種把握普遍性的活動內在統一起來,開創了一個普遍結果的科學技術時代。馬克思也深受其影響。
實踐和理論作爲人的活動在價值序列上相距最近,但它們所關涉的物件卻相距最遠。理論關涉的是一個必然的王國,而實踐關涉的是一個自由的王國,儘管自由王國是建基於必然王國之上的。對必然王國的認識可以邏輯地把握,但自由王國由於人的選擇因素的存在而沒有普適性的原理。出於這種區分,亞裏士多德對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作了明確的劃界。理論關涉的是“是” (being,即存在)的問題,實踐關涉的是“好” (good,即善)的問題。對“是”的追問可以直達“是之爲是”,[lvi]即上升到最高的普遍性;對“好”的解決則只能分而治之,那種柏拉圖式的“好”本身是不可實踐的,[lvi]對於實踐而言的“好”只能是具體的“好”。實踐和理論的這種分離所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實踐領域沒有普遍性,人類生活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價值基礎。該問題在近代爲康得所抓住,他發佈的絕對的道德律令所要解決的就是道德原則的普遍性問題。不過,在康得那裏,道德領域的普遍性跟科學知識的普遍性仍然是相互分割的,這就爲黑格爾哲學用絕對精神統一理論與實踐準備了課題。至此,馬克思離我們就不遠了。
我們將會看到,在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以及整個實踐思想中,亞裏士多德對人類活動的三分法及其實踐概念是如何起作用的,又是如何被創造性地轉化的,儘管本文不得不略去對有關概念與思想在中間兩千多年裏的演變情況的考察。
二、馬克思的實踐概念
1.勞動的實踐化和實踐的生産化
有了亞裏士多德思想作爲參照,有了西方實踐哲學傳統作爲背景,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馬克思的實踐從外延看既包括亞裏士多德的實踐也包括他所說的創制;其實質是勞動在價值上的實踐化和實踐在本質上的生産化。
先看勞動概念以及勞動的實踐化。
在亞裏士多德那裏,創制指一切目的在他的行動,其特徵是這種行動要製造或生産出東西來,並以這些東西作爲行動的目的。在此意義上,生産物質生活資料的勞動只是創制活動中的一種,而寫詩(poietikes)這樣的精神性活動也跟勞動一起列於創制活動(poiesis)之中。(順便一提的是,這兩種創制活動的區別後來成了海德格爾哲學的一個理論生長點。)不過,前已述及,亞裏士多德設定創制這個概念,是爲了將手段性活動安排到人類活動等級的最下層,以匹配古代希臘的社會分層。因此,生産物質生活資料的勞動仍然可以確認爲創制活動中的主要類別。
所有的創制活動都是生産性的,即都是要結出果實的,但勞動的生産性和其所結出的果實只跟人的肉體生存有關,而肉體生存只是人的各種有意義的活動的自然前提,它自身則不屬於有意義的活動。亞裏士多德明確講“生命屬於實踐而非創制”。[lvi]這樣一來,勞動及其生産性就只能具有手段和工具的性質,即目的在他的性質。本來,所有的創制活動都是目的在他的,即都是手段性的、工具性的,但勞動的手段性和工具性由於僅僅關乎肉體生存資料的生産,進而關乎一個龐大的從事這種活動的階級,因而蘊涵著重要的政治學結論。這個結論在亞裏士多德那裏很明確:勞動者階級是非勞動者階級(或者叫做“實踐者階級”、“理論者”階級)的手段和工具,非勞動者階級是勞動者階級的目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亞裏士多德把奴隸和幫手看成“使用工具的工具”,把使用奴隸和使用家畜看成一回事,把奴隸看成主人的財産的一部分,甚至看成其身體的延伸。[lvi]
到了馬克思那裏,勞動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這就是他所說的勞動的抽象化,即五花八門的勞動在市場經濟中變成了勞動一般或一般勞動(labour in general)。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專門討論了勞動在政治經濟學史上如何從一個指稱特定生産活動的概念變爲一個指稱一般勞動的概念。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馬克思又進一步討論了這個問題。這種抽象的一般勞動所對應的是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工業生産,即商品化和社會化的勞動。這種勞動的根本特點在於它被抽掉了一切特質而僅僅剩下生産價值和交換價值這一種特質,即變成了一種可以用貨幣來統一量度和換算的活動。勞動的這種變遷,使得“一切財富都成了工業的財富,成了勞動的財富,而工業是完成了的勞動”,並且,由於勞動及其果實依然表現爲非勞動者階級的私有財産,因而勞動的這種普遍化也就意味著私有財産的普遍化,從而私有財産就“完成了它對人的統治,並以最普遍的形式成爲世界歷史的力量”。[lvi]這個一般的勞動還具有使我們回過頭去透視歷史上的一切勞動形式的方法論意義。[lvi]
勞動的抽象化同時意味著勞動者的抽象化,即一個普遍的勞動者階級的形成。亞裏士多德時代的勞動還是分散的、個體形式的勞動,勞動者階級只是作爲一個等級而存在,決定誰成爲勞動者的因素不是勞動本身而是勞動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戰爭、債務和出生等。到了馬克思時代,勞動和資本的普遍化造成了勞動者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兩極對立。勞動者不再因爲任何別的原因而僅僅因爲創造價值、增殖資本對勞動的需求而成爲勞動者。“現代的工人只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他們的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性別和年齡的差別再沒有什麽社會意義了。他們都只是勞動工具”,“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裏來了”。[lvi]甚至連“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都變成了資產階級“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lvi]更重要的是,這個除了勞動一無所有的階級成了人口的大多數,他們所創造的財富和文明資源跟他們普遍的惡劣生存境況之間形成了最鮮明的反差,這種反差在當時極大地刺激著社會的價值良知。
馬克思稱勞動和勞動者的這種狀況爲“異化勞動”。他一方面肯定了勞動因抽象化而煥發的巨大力量及其歷史意義,另一方面否定了其歷來被賦予的手段性、工具性和奴隸性,從而否定了把勞動者當作手段、工具和奴隸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馬克思提供的理據是:任何物種的本質在於其生命的本質,而人作爲一個物種的生命本質就是他的生産性,意即人是一種將自己的生命本身作爲物件來加以生産的存在物,勞動就是這種生産生命的活動;既然如此,勞動就理應成爲它自己的目的,成爲生命本身的目的,而不應成爲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包括不應成爲資本家增殖資本的手段和工人活命的手段。[lvi]這樣一來,馬克思就在價值上將勞動提升到了亞裏士多德的實踐的地位,使勞動首次成了自爲目的的活動。
再看實踐的生産化。
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勞動、實踐、生産等概念是交替著使用的,他自己也從未在它們之間做出明確的界說。在沒有引入西方概念史背景的情況下,人們也只好按習慣來使用這些概念並隨意轉換。在瞭解亞裏士多德對人類活動的三分法及其傳統後,我們就可以較有把握地看到這樣幾點。第一,實踐概念包含勞動概念。馬克思所說的實踐基本上等於亞裏士多德的實踐和創制的總和,而勞動則是實踐的基礎性或根本性活動。在這點上,毛澤東把實踐分爲階級鬥爭、生産鬥爭和科學實驗不無道理。第二,勞動進入實踐範疇,使得實踐也獲得了勞動的一個根本特徵——生産性。在亞裏士多德那裏,生産是創制活動的主要特徵,是創制被打入另冊的一個主要把柄。但在馬克思這裏,生産是勞動的本質,進而是包括勞動在內的全部實踐活動的本質,甚至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質。第三,勞動的生産性是其他實踐活動的生産性的基礎。在亞裏士多德那裏,創制的生産性僅僅是實踐和理論的非生産性的手段,而在馬克思這裏,勞動的生産性直接決定著政治等行動的生産性,進而間接決定著思想的生産性。這也從一個角度反映了馬克思從異化勞動學說走向唯物史觀的內在理路。
亞裏士多德的實踐的非生産性和馬克思的實踐的生産性具有重要的對照價值。在亞裏士多德那裏,實踐是非生産性的,意味著倫理和政治活動的本質不在於生産新的倫理和政治樣態,從而倫理問題的實質只是德性問題,政治問題的實質只是公正問題。在馬克思這裏,實踐是生産性的,意味著不僅勞動生産著價值,而且在勞動基礎之上的政治活動還生産著新的政治形式和法律形式,道德活動也生産著新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以至整個人類社會都因爲這些活動的生産性而真正成了歷史性的存在和主體性的存在。不懂得馬克思的實踐概念的生産性,就很難領悟馬克思關於人是“他自己勞動的結果”[lvi]等類似說法的深意。不僅如此,正因爲包括政治活動在內的實踐具有生産性,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才獲得了足夠的理據。馬克思把巴黎公社看作“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lvi]從生産性角度看,無非是說政治活動的生産性可以反過來作用於勞動的生産性,或者說由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所生産出來的公社可以進一步推動和鞏固勞動的解放。可見,實踐的生産性是馬克思打開人類社會的歷史性的一把鑰匙。
2.實踐從必然通達自由之路
實踐的生産化蘊涵著實踐作爲活動和實踐所生産的物件作爲結果之間的關係問題,進而蘊涵著活動和結果何者爲手段何者爲目的的問題。按照馬克思的理想,實踐只有當其僅僅以自身爲目的時才是本真的、合理的,否則就是異化的、不合理的;對本真的實踐來說,它的結果不是對它的否定,而是對它的肯定,亦即二者都是目的,且結果之爲目的從屬於活動之爲目的。也就是說,實踐的生産性不僅不妨礙實踐在價值上充當目的,反而是對它充當目的的最好證明。果真如此的話,人的行動就不僅可以在價值上因其本身而配享自由,而且能夠在事實上因其結果而得到自由。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果包含全部人類行動的實踐跟它所生産的結果都成了目的,那麽,人類行動的手段性到哪里去了?
回顧一下亞裏士多德的觀點,我們就能明白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亞裏士多德看來,凡是要生産出結果的活動,結果肯定是目的,活動肯定是手段。這種情況下,從事活動的人就是手段,享受結果的人就是目的。人之所以不得不從事充當手段的活動,是因爲諸如生産勞動這樣的創制活動乃是自然加諸人的必然性強制,人無可逃避。沒有人心甘情願從事這種充當手段的活動,奴隸之所以被安排從事這種活動,是因爲他們跟主人具有“種屬差別”,本性使然。[lvi]可見,來自自然必然性的強制是人類手段性活動的根源,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領域就是社會通過讓一部分人去充當手段而跟自然必然性相抗爭的領域。這裏就預示了對人與自然的矛盾以及相關的人與人的矛盾的解決,必須最終放到物質生産領域來進行。
馬克思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借助黑格爾辯證法的程式力量,通過勞動的異化及其自我揚棄將這一十分繁難的問題處理爲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過程。在共産主義社會之前,作爲人的生命本質的勞動是以一種自我否定的形式存在的,表現爲勞動只是其産品的手段和工具,勞動者只是非勞動者的手段和工具。這就是勞動的自我異化,其頂點便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雇傭勞動。異化勞動的意義在於:這種手段性的活動能夠通過創造日益增長的物質財富,並且通過利用自然力征服自然力的方式來爲最終克服自然必然性準備條件。勞動異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轉變爲這種異化的自我揚棄。到那時,財富的極大豐富使勞動不再是出於自然對人的肉體生存的必然性強制,而是出於人自由發展自己生命本質的需要,人與人之間爲爭奪生存必需品的鬥爭將不再必要,一些人強制另一些人充當手段的問題也就解決了。[lvi]儘管馬克思承認物質生産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但他認爲,“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爲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lvi]
如是,亞裏士多德對之無可奈何的創制活動的手段性,特別是生産勞動的手段性,就被馬克思處理成了歷史過程的一個環節,並最終交還給了自然界自己。也就是說,通過勞動生産肉體生存所必需的物品,本來是自然界強迫人擔當而人又不願擔當的事情,到頭來竟然成了自然界自己的事情——自然界通過用它的一部分力量去控制其餘的力量來爲人類生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從而將人類從必然性中徹底解放出來,從充當手段、工具的處境中解放出來,從奴隸命運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爲完全目的性的存在物,亦即自由行動的存在物。
饒有趣味的是:亞裏士多德曾將奴隸看作“主人的一個部分”,看作獨立于主人“身體骨架之外的一個活著的部分”,[lvi]而馬克思則將自然界看作“人的精神的無機界”和“人的無機的身體”。[lvi]這樣對照之下,在實踐活動中解決人的普遍自由問題的樞機就顯露無遺了。
3.理論和實踐從分離走向統一
自然界憑什麽要聽人的擺佈,而將自己化作手段以成就人作爲目的的終極價值?或者說人靠什麽將自己當初不得不從自然界那裏接手的手段性成功交還給自然界?這些是由解決上面的問題所必然引出的問題。馬克思的答案很簡單:在於科學理論的神奇作用。在這裏,我們會清楚地看到,亞裏士多德在理論和兩種行動之間所劃出的界限被消除了,理論不再是兩眼朝天、跟實踐與創制無關的活動,而成了人類在全部實踐中獲得徹底解放的關鍵因素。
亞裏士多德三分人類活動時,把理論、科學知識放在最高貴的位置上,但惟其高貴,它們才無須通過作用於實踐和創制而證明自己的價值,因而也就無所實用於人們的實際生活。直到弗·培根,高貴的理論和實用的技藝才被建構爲原理和應用的關係。在培根那裏,人類知識體系首先分爲“記憶”(歷史)、“想象”(詩歌)和“理性”(自然神學和哲學);哲學又分爲“自然哲學”和“人類哲學”;自然哲學再分爲“觀察的自然哲學”和“致用的自然哲學”;人類哲學分得更細,但幾乎每一支脈到頭來都既包括相關的理論也包括相關的技藝,如倫理學就既包括“善的本質”也包括“善的培植”。[lvi]培根在自然哲學領域所建立的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藝之間的聯繫直到今天仍然有效,並且已經牢不可破,但他在人類哲學領域所建立的類似聯繫卻受到了休謨關於“是”和“應該”之間不能相互推導的觀點[lvi]的挑戰。這一挑戰促使康得將“自然哲學”和“道德哲學”嚴格區分開來,並進而將“根據自然概念是實踐的東西”和“根據自由概念是實踐的東西”嚴格區分開來。[lvi]康得的做法客觀上將培根在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實踐之間的聯結固定下來,並讓這個領域脫離了道德的約束。同時,康得將道德實踐跟生産性的技藝活動脫鈎,進一步強化了亞裏士多德實踐的非生産性,從而使倫理和政治領域的問題仍然局限在規範性問題上。黑格爾用辯證的方法破除了先前對人類知識和活動的各種僵硬區分,並通過將它們安排爲絕對理性自我演進的不同環節而最終一統天下。
跟黑格爾一樣,馬克思是人類活動、人類知識的統一論者;他和黑格爾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是用作爲生産性行動的實踐來統一這一切的。在馬克思這裏,儘管實踐可以區分爲不同的活動形式,但其本質是一樣的。與此相應,儘管理論也有內部的劃分,但其得以成立的標準也是一樣的。在此前提下,馬克思將理論與實踐內在關聯起來,並且通過把理論看作實踐的一種品質和一個環節而確立了實踐對於理論的優先地位。這一點從馬克思將人的生命本質規定爲“自由的自覺的活動”就能看清楚。所謂“自覺的”,就是有意識的,並且是在“知類”的抽象程度上來認識世界的,[lvi]因而也就是理論的。馬克思這樣規定理論,並非貶低理論,而是賦予了理論對於實踐的必不可少的意義。
具體說來,理論對實踐的意義可分爲兩方面:其一是自然科學理論對變革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實現勞動解放的意義,其二是馬克思主義作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對於共産主義運動的意義。
對自然科學的巨大歷史作用,馬克思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說:“自然科學通過工業的媒介愈加實踐地(more practically)侵入並轉變人的生活,儘管其直接後果不得不是對人的非人化的加劇,但它卻準備了人的解放。”[lvi]到了《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馬克思更加詳盡地發揮了這一思想。他的論證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財富的創造越來越多地取決於“科學在生産上的應用”;“工人不再是生産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産過程的旁邊”;大機器“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物件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麽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産力”;“於是,資本就違背自己的意志,成了爲社會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創造條件的工具”。[lvi]可見,科學在人的解放中所扮演的角色何等重要。
回頭再看看亞裏士多德,我們就會發現事情的一種奇妙的顛倒。亞裏士多德高度評價理論活動,是因爲理論活動是人對自由時間即閒暇的自由享用。“幸福存在於閒暇之中”,“理智的活動則需要閒暇”,閒暇是人追求不朽、追求過神的生活、獲得最高幸福的起碼條件。[lvi]但在那個時代,煩忙是常態,閒暇不易得,多數人只能終日忙碌,只有少數人能得閒暇。或者說,自由時間是當時最爲稀缺的資源。於是,從事理論就成了一種至高的奢侈,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在馬克思這裏,理論和閒暇的關係完全顛倒過來了:不是閒暇産生理論,而是理論産生閒暇;不是理論在消耗閒暇這種稀缺資源,而是理論的生産性在消除閒暇的稀缺性,在將閒暇變成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取用的公共資源。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就成了節約勞動時間而增加自由時間的科學。自由時間的增加意味著個人的充分發展,尤其意味著智力活動、理論活動的發展,而這又反過來成爲進一步節約勞動時間、增加自由時間的動力機制。[lvi]在這種螺旋式上升的良性迴圈中,人類的自由王國就到來了。到那時,理論、實踐、創制的傳統界限將徹底消失,勞動的手段性、工具性、奴隸性將被洗刷乾淨,它的生産性、自由自覺性、目的性將得到充分的發揚,在這個意義上,勞動將成爲所有的人類活動的代名詞,成爲人的第一需要。
那麽,是否單靠自然科學的力量就能實現人的自由呢?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馬克思始終是把科學力量的發揮置於資本運行的邏輯中來加以規定的,科學運用於大機器生産的意義只是在於提供資本主義終結的物質條件,最後時刻新舊社會的轉換還得訴諸“使現存世界革命化”[lvi]的無產階級革命,而從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成熟的共産主義社會還離不開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作爲科學理論的作用在於揭示其中的規律,指出事情演變的方向,確立奮鬥的目標,爲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提供行動指南。或者說,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就是人類實踐、特別是無產階級的政治實踐所內在要求和必然産生的自我意識和根本要素。馬克思將舊哲學的本質歸結爲“解釋世界”,並提出“問題在於改變世界”,[lvi]便是對自己學說的這種使命的理論自覺。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無產階級政治實踐的意義跟自然科學理論對於資本主義機器生産的意義具有共同的思維結構和推論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科學,自然科學理論也是科學,它們都作爲相關實踐活動所不可或缺的關鍵性因素在起作用,都在人類社會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最後一躍中扮演著推動力的角色,而馬克思主義理論更是最後之一推。這就是馬克思對自己理論的根本定位。
根據馬克思的邏輯,到了共産主義社會,自然科學不再服務於資本,而是直接服務人的自由,同時,人的科學也不再局限于道德和政治這些傳統領域,亦即不再把自由僅僅看作一些特定生活領域的事情,而是將自由還原到人的自然本性中去把握,這樣一來,自然科學和人的科學就會變成“一門科學”,[lvi]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自然科學理論也會有機地融爲一體。到那時,所有的科學理論統一而且向著未知領域開放,所有的實踐活動和諧而且自由發展,以至於理論作爲自由的自覺的生産性活動跟實踐之間就不再有任何實質性的區別,從而理論便通過變成實踐活動中的一種而跟實踐實現了最後的統一。
至此,馬克思就完成了他的實踐概念,也完成了他對西方實踐哲學傳統的根本性改造。實踐在亞裏士多德那裏還主要是一個倫理學概念,而到了馬克思這裏就已經具有了本體論的性質,它在哲學邏輯上的潛能也就發揮到了頂點。這兩個實踐概念隔著兩千多年的西方思想史而遙相對峙,其間的巨大張力正成爲激發當代實踐哲學思考的一個重要機制。
在馬克思之後,西方實踐哲學的主流是從馬克思回歸亞裏士多德,即從人類活動的實踐統一性回歸實踐跟其他活動的區分。不論是海德格爾對藝術和技術這兩種技藝的再區分,還是加達默爾對亞裏士多德三分法的重申,也不論是阿倫特把人類活動分爲“勞動”、“工作”和“行動”,還是哈貝馬斯將人類活動分爲“勞動”和“相互作用”,[lvi]都表明了這一點。這似乎也應驗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古話,至於其中的深層原因,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去探察了。
結語
本文的觀點可以概述如下。
1.西方哲學中存在著一個源遠流長的實踐哲學傳統,亞裏士多德是這一傳統的開創者,馬克思的實踐哲學是對該傳統的繼承和創造性轉化,當代西方各種實踐哲學是這一傳統的較新樣態。西方實踐哲學傳統有其特定的和連續性的理論問題群,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理論派別所關注的問題之間都存在這樣那樣的關聯。理解當代西方實踐哲學固然不能脫離這個傳統,理解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同樣不能撇開這個傳統。只有在這一傳統的總體背景上,我們才能較爲確當地爲各種具體理論定位。
2.西方實踐哲學産生於亞裏士多德,是因爲直到那時,一個既不能納入自然必然性的解釋框架也不能納入理念必然性的解釋框架的人類生活領域,即人的倫理和政治行動的領域,才從學理上呈現出來。在這個領域中,人們不是由於自然必然性的強制而行動,因爲他們可以自主選擇;也不是按照理念的統一性要求而行動,因爲任何理念在規範人類行動上都達不到普遍有效性。對這個特殊領域,究竟應當如何理解,如何對待?便成爲亞裏士多德率先加以研究的問題。這也就是既不同于本原問題也不同於理念問題的實踐問題。
3.對亞裏士多德來說,實踐問題只是他所研究的問題之一,並且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對亞裏士多德的實踐哲學,不能將其從他的哲學整體中切割下來單獨理解,而只能將其放在他的哲學整體中去理解。亞裏士多德將人類活動區分爲理論、實踐與創制。理論把握事物的原因和原理,求知普遍性和必然性,進而跟永恒的神性相契合。這是有閒暇的人自由從事的活動,是以自身爲目的的活動,因而是最高貴的活動。創制主要指生産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行動。這是人類出於自然必然性的強制而不得不從事的活動。它以産品爲目的,自身只是手段,因而是最低賤的活動,主要由奴隸來承擔。實踐指免於生産勞作的人們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行動,主要包括倫理和政治行爲。這些行動具有自由選擇性,並且以自身爲目的,但由於它們不得閒暇,不能達到普遍性,因而在價值上次於理論活動。如是,亞裏士多德就爲西方思想制定了三塊模板:“理論模板”——“(自由的)理論(通過)→(目的在己的)思想(求知)→自然(的必然)”;“實踐模板”——“(自由的)實踐(通過)→(目的在己的)行動(實現)→社會(的應然)”;“創制模板”——“(不自由的)創制(通過)→(目的在他的)行動(克服)→自然(的必然)”。在某種意義上,後世的西方實踐哲學都可以解釋爲對這三塊模板的修補、剖分、拆解、拼裝或改鑄。
4.弗·培根成功地將亞裏士多德的“理論模板”和“創制模板”粘貼起來,組成了通行至今的“科學—技術模板”,但他以同樣的手法粘貼“理論模板”和“實踐模板”卻沒有成功。康得則取消了“創制模板”的獨立性,而將其歸併到“理論模板”,這跟培根的“科學—技術模板”有微妙區別,同時再將“理論模板”和“實踐模板”明確區分開來,並將後者置於前者之上。黑格爾的工作是將這三塊模板辯證地統一起來,但其統一的基準實際上是“理論模板”。這些都是在馬克思之前對亞裏士多德的實踐哲學傳統的重要改造,對馬克思都産生了直接的影響。
5.馬克思的實踐概念的最根本的特徵是將“實踐模板”和“創制模板”統一起來,並且將後者看作前者的基礎,將前者看成後者的本質。這在哲學史上無疑是一種創新。一方面,馬克思把生産勞動作爲實踐的首要內容,把其他人類行動置於生産勞動的基礎之上,把生産勞動的生産性看成整個實踐活動的普遍屬性,把包括物質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內的整個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看成人類的實踐活動的生産性結果,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看成綻放人類實踐的生産性潛力的特殊機制和達到理想狀態的必經環節,把共産主義看成人類實踐的生産性獲得徹底解放的生活形式。另一方面,馬克思把人的本質規定爲生産性的生命,並把這種生産性生命的自由的自覺的全面發展看作人類生活的最高目的,從而賦予了生産勞動前所未有的價值地位。這實際上就是將先前只被看作手段的勞動從價值上提升到作爲目的的實踐的高度。不僅如此,馬克思還將勞動本應是目的卻實際上充當手段的現象理解爲一種歷史性現象,亦即將勞動從充當手段到充當目的的變化過程看成勞動自身的一種辯證運動過程,從而將人類的勞動史、實踐史理解爲人類通過自己的生産性活動不斷克服自然界強加給人的手段性並最終達到所有的人都同等地成爲目的的歷史。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還賦予了傳統意義上的倫理和政治實踐以能動地位,特別是把階級鬥爭看作歷史的杠杆,把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看作勞動解放的必要的政治形式。同時,科學理論,包括自然科學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發展、勞動解放過程中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所有這些活動,到了共産主義社會,都將因具有同樣的生産性和自由自覺品質而成爲實踐。這樣一來,馬克思就將“理論模板”一併整合進了前兩個模板的統一體中,從而實現了三個模板在目的在己的生産性行動基礎上的統一。
6.從亞裏士多德到馬克思,實踐概念的演化呈現出一種由分到合的趨勢。培根粘貼“理論模板”和“創制模板”無疑是合,康得將“創制模板”歸併到“理論模板”又何嘗不是合,黑格爾將三塊模板暗合於“理論模板”更是一種合,馬克思最終在“實踐”的名義下統合三者,更是將實踐的合的邏輯發揮到了極致。在馬克思之後的現代西方哲學中,實踐概念的演化則主要呈現出分的趨勢,到後現代思潮中達到另一極端。
綜上所述,本文以西方哲學史爲總體背景,較爲詳細地探討了亞裏士多德的實踐概念和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及其內在關聯,並旁及了大量相關的理論線索,爲有關研究領域中的進一步操作確定了兩個重要的基準點。在筆者有限的檢索範圍內,儘管研究同類課題的文獻(包括英文文獻)並不算少,本文也引用了一些,但這些文獻大多長於描述,而鮮能將亞裏士多德思想和馬克思思想的內在精神加以貫通地理解,尤其對馬克思的思想普遍缺乏深切的體悟。有鑒於此,本文的分析應有足夠的新意。當然,由於筆者學養有限,對哲學史的理解可能會有不少問題,誠望專家們不吝賜教。
[lvi] 伽達默爾著:《科學時代的理性》,薛華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77頁。 [lvi] 如張汝倫著:《歷史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洪漢鼎著:《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張能爲著:《理解的實踐——伽達默爾實踐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lvi] 參見麥金太爾著:《德性之後》,龔群、戴揚毅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lvi] 嚴格說來,亞裏士多德關於實踐的思想是不能叫做“哲學”的,理由另文申述,本文姑且襲用成說。 [lvi] 參見汪子嵩等著《希臘哲學史》1第七章(作者:陳村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0頁。 [lvi] 參見Rogger Trigg: Ideas of Human Nature, Blackwell Publishers, Malden, 1988, p. 6. 中國學者中,陳村富教授對有關問題做過相當深入的探討,參見汪子嵩等著《希臘哲學史》2第四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頁等處。 [lvi] 參見汪子嵩等著《希臘哲學史》1,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頁。 [lvi] 在《斐德羅篇》,參見Nichlas Lobkowicz: Theory and Practice: History of a Concept from Aristotle to Marx,University of Noter Dame Press, London, 1967, p. 3. [lvi] 在《斐萊布篇》,參見汪子嵩等著《希臘哲學史》2,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9頁。 [lvi] 參見汪子嵩等著《希臘哲學史》1,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頁。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形而上學》1025b,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1, p. 778. [lvi] Nathan Rotenstreich: Theory and Practice,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1977, p. 18. [lvi] 參見苗力田主編:《古希臘哲學》中的巴門尼德著作殘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頁。 [lvi] 參見Nicholas Lobkowicz: Theory and Practic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London, 1967, P. 14.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形而上學》1072b,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頁。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尼各馬可倫理學》1095b,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等處。 [lvi] 參見Nicholas Lobkowicz: Theory and Practic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London, 1967, P. 9.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尼各馬可倫理學》1094a,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政治學》1253b-1254a,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9頁。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形而上學》1026a,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頁;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edited by Richard McKeon,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1, p. 779.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尼各馬可倫理學》1181b,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頁;Nicomachean Ethics, Dover Publication, Inc., New York, 1998, p. 199. [lvi]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edited by Richard McKeon,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1, p. 779.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形而上學》981b,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尼各馬可倫理學》1177b,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頁。 [lvi] 參見Nicholas Lobkowicz: Theory and Practic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London, 1967, P. 22.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形而上學》981a-b,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頁。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形而上學》1026a,吳壽彭譯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20頁。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優台謨倫理學》1218a,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頁。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政治學》1253b,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9頁。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政治學》1253b、1254b、1255b,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9、11、14頁。 [lvi] 參見馬克思著:《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116頁。 [lvi] 參見馬克思著:《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頁。 [lvi] 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80頁。 [lvi] 參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頁。 [lvi] 參見馬克思著:《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頁等處。 [lvi] 參見馬克思著:《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頁等處。 [lvi] 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9頁。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政治學》1259b-1260a,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頁。 [lvi] 參見馬克思著:《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頁。 [lvi] 參見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頁。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政治學》1255b,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頁。 [lvi] 參見馬克思著:《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頁。 [lvi] 參見餘麗嫦著:《培根及其哲學》,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157頁。 [lvi] 參見休謨著:《人性論》,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09-510頁。 [lvi] 參見康得著:《判斷力批判》上卷,宗白華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8-9頁;並參見The Essential Kant, the New English Library Limited, London, 1970, p. 388-389. [lvi] 參見馬克思著:《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97頁。 [lvi]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3,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5, p. 303. [lvi] 參見馬克思著:《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手稿後半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3頁。 [lvi] 參見亞裏士多德著:《尼各馬可倫理學》1177b-1178a,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228頁。 [lvi] 參見馬克思著:《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手稿後半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08頁。 [lvi]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頁。 [lvi] 參見馬克思著:《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頁。 [lvi] 參見馬克思著:《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頁。 [lvi] 參見俞吾金著:《如何理解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哲學研究》2002年第11期。主要參考文獻:
汪子嵩等:《希臘哲學史》1、2,人民出版社,1997年、1993年。
Rogger Trigg: Ideas of Human Nature, Blackwell Publishers, Malden, 1988.
Nichlas Lobkowicz: Theory and Practice: History of a Concept from Aristotle to Marx, University of Noter Dame Press, London, 1967.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1.
Nathan Rotenstreich: Theory and Practice,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1977.
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吳壽彭譯本,商務印書館,1959年。
亞裏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
Nicomachean Ethics, Dover Publication, Inc., New York, 1998.
亞裏士多德:《政治學》,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
亞裏士多德:《優台謨倫理學》,苗力田主編:《亞裏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3,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5.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手稿後半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